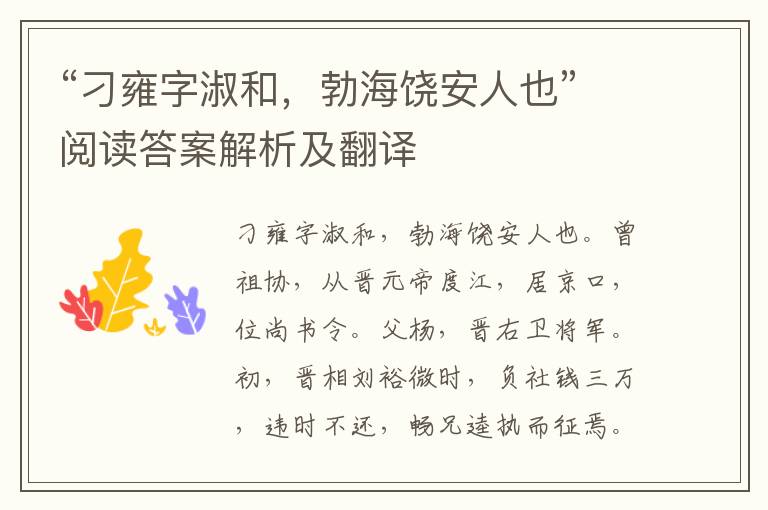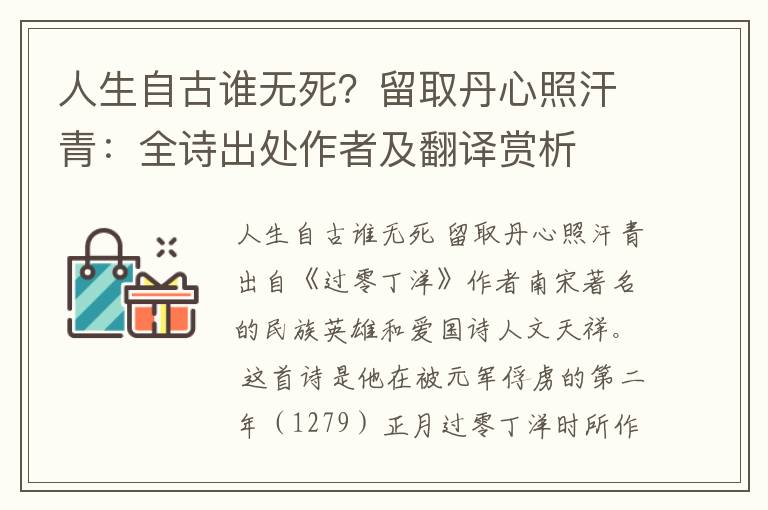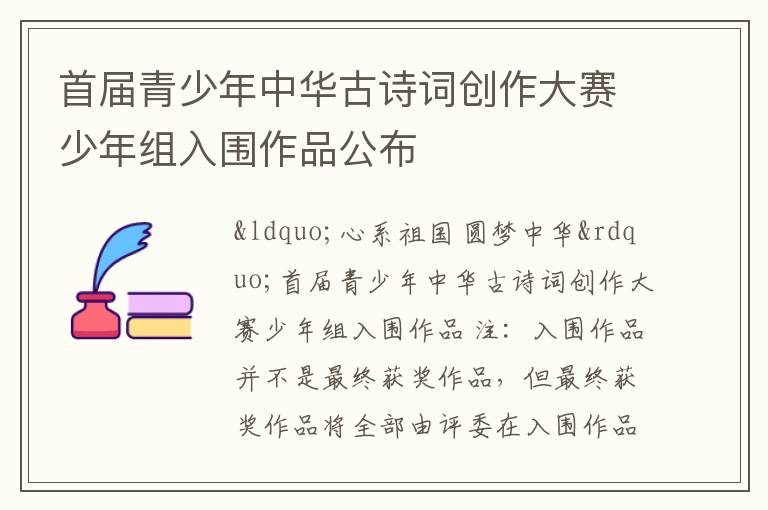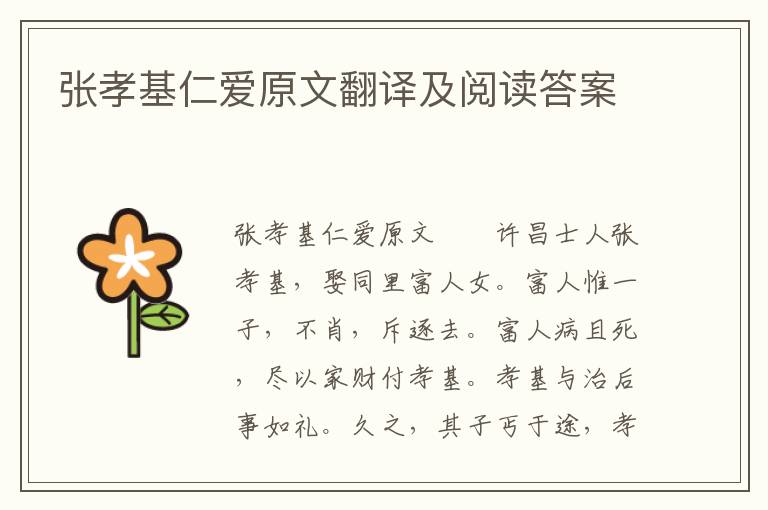【简介】感谢网友“雕龙文库”参与投稿,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方便大家学习。
古墙行
建炎白马南渡时,循王以身佩安危。
疏恩治第壮舆卫,缩板栽榦由偏裨。
下锸江城但沙卤,往夷赤山取焦土。
帐前亲兵力如虎,一日连云兴百堵。
引锥试之铁石坚,长城在此势屹然。
上功幕府分金钱,欢声如雷动地传。
尔来瞬患逾百年,高崖为谷惊推迁。
华堂寂寞散文础,乔木惨淡栖寒烟。
我入荒园访遗古,所见惟存丈寻许。
废坏终嗟麋鹿游,飘零不记商羊舞。
王孙欲言泪如雨,为言王孙毋自苦。
子孙再世隳门户,英公尚及观房杜。
如君百不一二数,人生富贵当自取,
况有长才文甚武。公侯之后必复初,
好把家声继其祖。
“建炎自马南渡时,循王以身佩安危”交待昔时修筑府第的背景。一一二七年一月,金兵攻破北宋京城开封,俘虏徽宗、钦宗。金军退出开封后,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于同年五月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是为宋高宗,年号“建炎”,后来赵构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传说中有“泥马渡康王”的故事,故此诗中称为“建炎白马南渡时”。“循王”指南宋初年抗金名将张俊。张俊曾劝赵构南渡,据江为险;南渡后,张俊平定苗傅、刘正彦等反叛,又屡破金人进犯,屡建战功,最为高宗所器重,死后追赠循王,故诗中称为“以身佩安危”。
因为张俊功重一时,绍兴十三年(1144年),“敕修甲第,遣中使就第赐宴,侑以教坊乐部”(《宋史》本传)。“疏恩治第壮舆卫”以下十句即指此事。高宗下达恩命,为张俊修治府第,以壮其车马护卫。“缩板栽榦由偏裨”。可见工程重要,全由将士动手,不用民侠。板榦,都是筑城工具,偏、裨,指将佐卫士。“下锸江城但沙卤,往夷赤山取焦土”,说明了建造循王府第工程的浩大。修建府第必须使用大量的土石,筑第的将士在杭州这座滨江城市下锸(锹),但疏松的沙土和碱土又不适宜,所以必须搬运土石。“夷”指削平;“赤山”本是传说中的山名,此指大山。因其名“赤山”,故想像其土为“焦土”。“帐前亲兵力如虎,一日连云兴百堵”。张俊手下兵将个个力壮如虎,一天之间,百堵高墙便拔地而起,耸入云端。这里接连用了两个夸张手法:削平大山用于筑墙,说明府第工程浩大;府墙高入云端,拔地而起,说明它气势宏伟。那么府墙的坚固程度如何呢?“引锥试之铁石坚,长城在此势屹然”。相传十六国夏王赫连勃勃筑统万城,每块土方皆用锥刺之,刺入则杀筑者,不入则杀刺者,以故城坚固无比。“引锥”句暗用此典。拿大铁锥来刺击试验,府墙就像铁石一样坚固;又如同稳固无比的万里长城一样,高高屹立在天地之间。紧接上文的两个夸张,这两句又连用两个比喻,更进一步渲染府墙的坚固和气势。这样,两个夸张,两个比喻,把府墙的不凡声势和无比坚固描绘得淋漓尽致。“上功幕府分金钱,欢声如雷动地传”,描述府第建成之后,论功行赏,上下欢声雷动,可见颁赏之多,从而侧面烘托出了筑第费用之大。总之,这一部分调动了诸多艺术手法,选择了修建府第时筑墙这个重点,从不同侧面加以烘托,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印象:如此宏伟坚固的府第,一定能永久地屹立在天地之间,经受得住万古的风吹雨打。然而,诗的下半部却陡然一转,描绘了一幅极其荒凉破败的景象。
“尔来瞬息逾百年,高崖为谷惊推迁。”历史的长河日夜奔腾,瞬息之间百年已逝。高崖为谷,沧海桑田,那宏伟坚固的循王府第于今又在哪里?“华堂寂寞散文础,乔木惨淡栖寒烟。”夕日繁华的殿堂已死气沉沉,雕饰的墙基散漫朽烂;堂前的故国乔木,唯有寒烟阴雾缭绕其间。“我入荒园访遗古,所见惟存丈寻许”进一步描绘府第的巨大变化:府墙本来高入云端,势如长城,而今却只剩下丈把来高;本来是坚如铁石,威如大山,而今只留下败堵残垣;本来是亲兵如虎,欢声雷动,而今却人迹罕至,一片飘零。这种反差太大了,不能不使人感慨万端。“废坏终嗟麋鹿游,飘零不记商羊舞”两句意蕴相当深刻。“麋鹿游”用吴王夫差亡国、姑苏台上见麋鹿游之典。“商羊”是传说中的鸟名,大雨前,此鸟常屈一足起舞。汉代刘向《说苑·辨物》篇载:“齐有飞鸟,一足,来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又使聘问孔子。孔子日:‘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沟渠,天将大雨。’于是如之,天果大雨。”诗中运用此典,加深了感慨之情。商羊是能够预知风云变幻的灵物,但处于繁盛时期的人们却忘记了它,因此对世事的盛衰不能预知。一旦盛极衰来,只能面对荒园野鹿、破败凋零,发出无可奈何的慨叹。诗人在这里流露出的居荣思辱的感慨,也是对世事变幻的无奈:既使能够预知,又该能如何呢?世事毕竟是要变迁的啊!
出于这种无奈和感慨,诗人对“王孙”即张俊的后人进行了劝慰和开导。“王孙”株守在废第里,偶见诗人经过问询,自不免欲言未言、已泪下如雨。对此,诗人劝慰道:你不要太感痛苦了,想大唐贞观的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生前相业何等隆赫,其子房遗爱、杜荷都娶了公主,但两位贤相一死,不久其子便或被杀、或流放,家声大跌。无怪目睹其事的另一位唐初功臣李勣(封英国公),在临终前感叹道:“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辛苦作得门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儿,破家荡尽。”(《旧唐书·李勣传》)可见,名臣之后,再世而隳毁其家,实是常事;像王孙您这样尚能留居旧第,已是百不存一二、非常可贵难得的了。人生要自取富贵,不能依赖先人余萌,您有文武长才,又是公侯名门之后,定能重振门户、绳武乃祖的。这一段话,在全诗占了三分之一篇幅,可见诗人感慨良深。另外,这一段其实也是诗人对于富贵显达的态度的流露。杨载中年以后才以布衣召为国史院编修官,最终也未能显达,他的诗歌中经常流露出对飞黄腾达的渴求。因此,他在本诗的结尾处才不厌其烦地鼓吹富贵荣华、光宗耀祖。这从一个侧面,亦可展示元代知识分子的深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