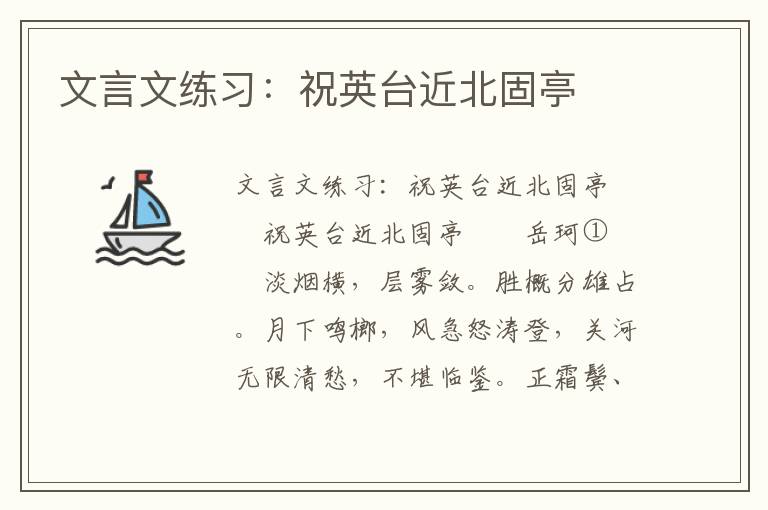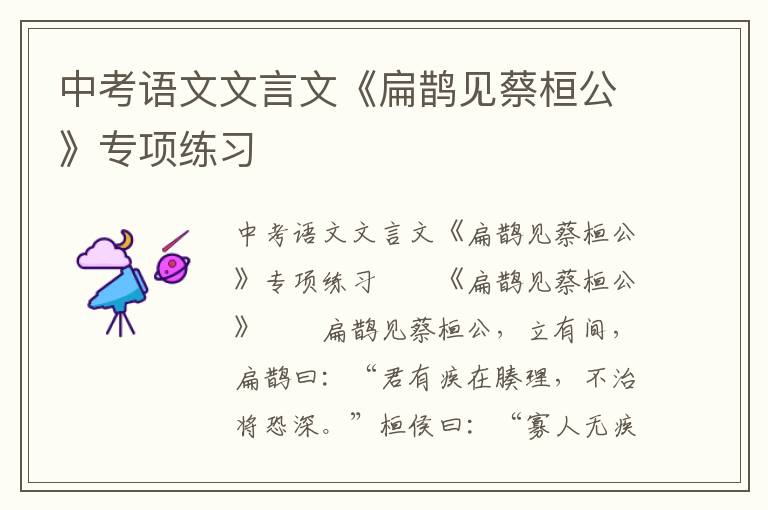【简介】感谢网友“雕龙文库”参与投稿,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方便大家学习。
李白《长门怨二首》
胡应麟在《诗薮·内编》中论说绝句时,曾以李白的《长门怨》与王昌龄的《西宫春怨》相对照,认为:“李则意尽语中,王则意在言外。然二诗各有至处,不可执泥一端。”下面是李白的《长门怨二首》:
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
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
桂殿长愁不记春,黄金四壁起秋尘。
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
据《乐府解题》记述:“《长门怨》者,为陈皇后作也。后退居长门宫,愁闷悲思。……相如为作《长门赋》。……后人因其《赋》而为《长门怨》。”陈皇后,小名阿娇,是汉武帝后。武帝小时曾说:“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李白的这两首诗采用这一乐府旧题来写宫人的愁怨。两诗表达的是同一主题,分别来看,运思、布局,各不相同,合起来看,又有珠联璧合之妙。
第一首,通篇写景,不见人物。而景中之情,浮现纸上;画外之人,呼之欲出。诗的前两句“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点出时间是午夜,季节已入凉秋,地点则是人去楼空、荒旷冷寂的“金屋”。唐人用《长门怨》题写宫怨的诗很多,意境往往有相似之处。沈佺期的《长门怨》有“玉阶闻坠叶,罗幌见飞萤”句,张修之的《长门怨》有“玉阶草露积,金屋网尘生”句,都是以类似景物来渲染环境气氛,但远远比不上李白的这两句诗。这两句诗有强烈的感染力量,上句着一“挂”字,下句着一“流”字,给人以异常凄凉之感,从而收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标举的“境界全出”的艺术效果。
诗的后两句“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点出题意,通过月光引出愁思。沈佺期、张修之的《长门怨》也写到月光和长门宫殿。沈诗中有两句是“月皎风泠泠,长门次掖庭”,张诗中有两句是“长门落景尽,洞房秋月明”,写得都比较平实板直,也不如李白的这两句诗之超妙深曲。本是宫人见月生愁,或是月光照到愁人,但这两句诗却不让人物出场,把愁说成是月光所“作”,运笔空灵,设想奇特。前一句,妙在“欲到”两字。“欲到”,可解为“将要到”;在此处也不妨解为“想要到”,似乎月光自由运行天上,有意到此作愁。后一句,妙在“别作”两字。它的言外之意,既可以是,深宫之中,愁深似海,月光照处,遍地皆愁,到长门殿,只是“别作”一段愁而已;也可以理解为,宫中本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乐者自乐,苦者自苦,正如裴交泰的一首《长门怨》所说,“一种蛾眉明月夜,南宫歌管北宫愁”,月光先到皇帝所在的南宫,照见欢乐,再到长门,“别作”愁苦。
从全篇看,这首诗展示的是一幅以斗柄横斜为远影、以空屋飞萤为近景的月夜深宫图。境界是这样阴森冷寂,读者不必看到这深闭在长门宫中的人,而其人的处境之苦、愁思之深已经可想而知了。
第二首诗,着重言情。通篇是以我观物,缘情写景,使景物都染上极其浓厚的感情色彩。上首到结尾处才写到“愁”,这首一开头就揭出“愁”字,说明下面所写的一切都是愁人眼中所见、愁人心中所感。
诗的首句“桂殿长愁不记春”,不仅揭出“愁”字,而且这个愁是“长愁”,也就是说,诗中人并非因当前秋夜的凄凉景色偶然引起愁思,乃是长年都在怨愁之中,即令春临大地,万象更新,也丝毫不能减轻这种怨愁,而由于怨愁难遣,她是感受不到春天的,甚至在她的记忆中已经没有春天了。诗的第二句“黄金四壁起秋尘”,与前首第二句遥相绾合。因为“金屋无人”,所以“黄金四壁”生尘;因是“萤火流”的季节,所以是“起秋尘”。下面三、四两句“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又与前首三、四两句遥相呼应。前首写月光欲到长门,是将到未到;这里则写明月高悬中天,已经照到长门,并且让读者最后在月光下看到了“长门宫里人”。
这位“长门宫里人”对季节、对月光的感受,都是与众不同的。春季年年来临,而说“不记春”,似乎春天久已不到人间;明月高悬天上,是普照众生的,而说“独照”,仿佛“月之有意相苦”(唐汝询《唐诗解》中语)。这些都是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所说的“无理而妙”,以见伤心人别有怀抱。
这两首诗的后两句与王昌龄《西宫秋怨》诗末句“空悬明月待君王”一样,都出自司马相如《长门赋》“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但王诗中的主角是在愁怨中仍然希冀得到君王的宠幸,命意并不可取。李诗则活用《赋》语,另成境界,虽然以《长门怨》为题,却并不拘泥于陈皇后的故实。诗中呈现的是在人间地狱的深宫中过着孤寂凄凉生活的广大宫人的悲惨景况,揭开的是冷酷的封建制度的一角。
对李白的这两首诗,萧士赟在《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中注云:“此诗皆隐括汉武陈皇后事,以比玄宗皇后。”梅鼎祚在《李诗钞评》中不以萧说为然,认为此诗或李白“自况”,并说:“古宫怨诗,大都自况。”这两说,都不可取。古代封建帝王为满足个人的声色之欲,任意扩大后宫嫔妃人数,每个朝代总有大批民间少女被选入宫,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终身失去自由和幸福。这样一个问题,必然要反映到文学中来,因而宫怨诗也就大量产生了。一些宫怨诗的可贵之处,正在其抨击了这一“后宫佳丽三千人”(白居易《长恨歌》)的罪恶制度,表达了作为一个诗人所应具有的同情心。对这两首《长门怨》,似也应从这一角度进行评价。萧说固然有穿凿附会之嫌,梅说也没有提出有说服力的论证。尽管李白一生怀才不遇,与宫人之虚度青春在某一点上有相同之处,但通观李白的经历和生活,联系他的开朗的性格、洒脱的胸襟,当他表达自己的愤懑不平时,往往发为“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以及“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之类的豪语,而不会自比于被深闭在冷宫中的宫人,作如此凄楚幽怨的苦语。至于“古宫怨诗大都自况”的推论,更不免近乎武断。当然,一个失意的诗人更容易同情他人的痛苦,当他以宫怨为题材进行写作时,也能较真切地设想宫人的处境和怨情;但同情与“自况”,究竟是两回事,并不能混为一谈。总之,萧、梅两说似都难成立。李白只是借《长门怨》这一乐府旧题泛写被禁闭在深宫中的广大宫人的深愁苦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