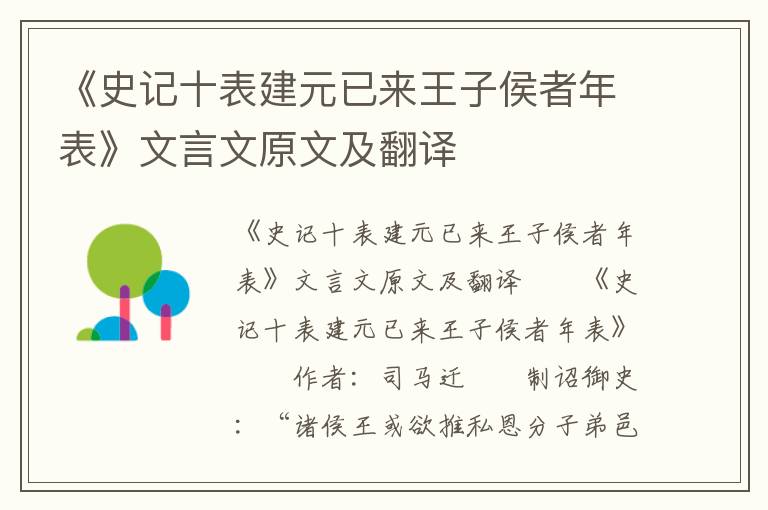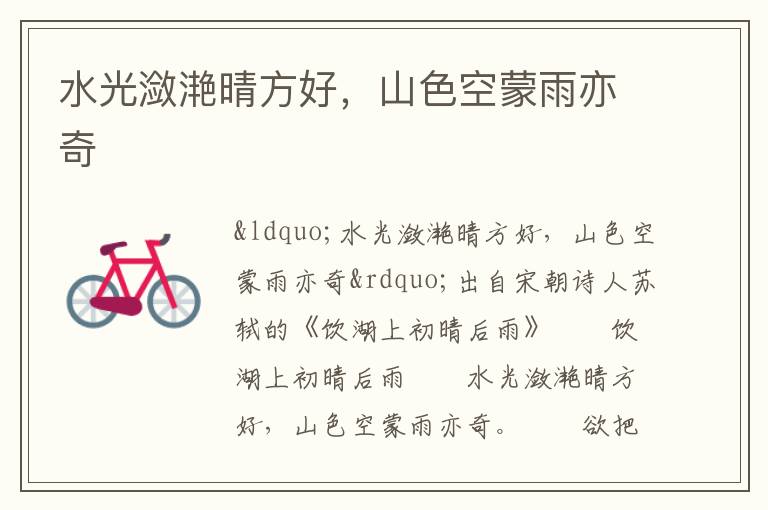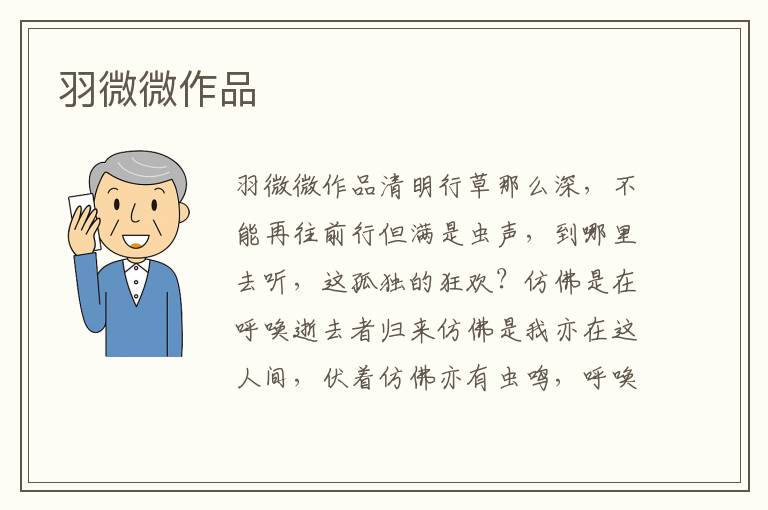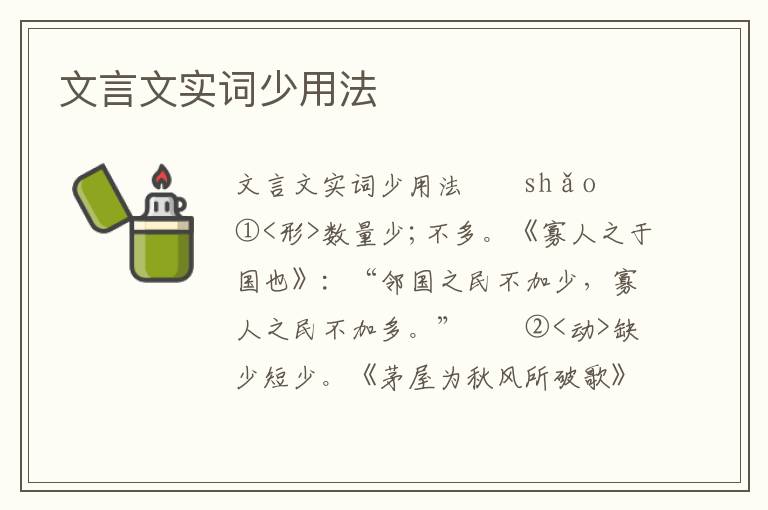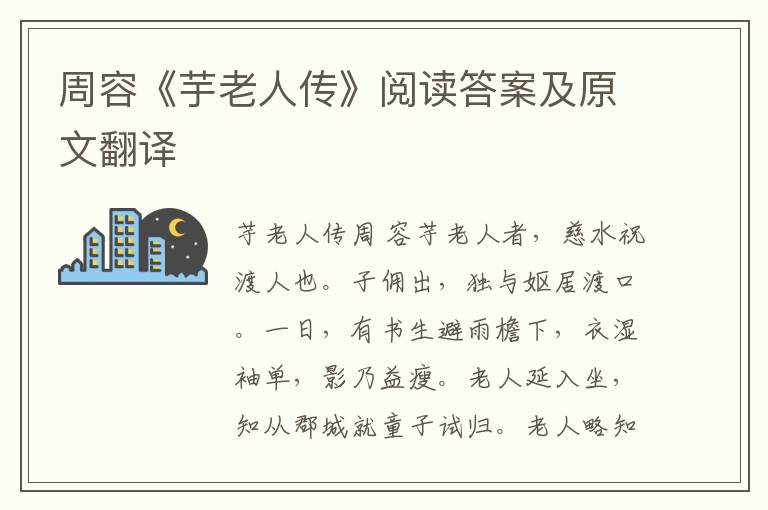【简介】感谢网友“雕龙文库”参与投稿,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方便大家学习。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②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③。
谁见幽人独往来④?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⑤,寂寞沙洲冷⑥。
【注释】
①卜算子:词调名。又名缺月挂疏桐、百尺楼、楚天遥、眉峰碧等。双调,仄韵。此词四十四字,两段各四句两仄韵。
②黄州定惠院:见《寓居定惠院之东……》诗注①
③漏:指更漏,古代用水计时的器具。漏断:漏壶里的水滴完,指夜深。
④幽人:《易·履卦》:“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原指幽囚之人,这里引申为幽居之人。苏轼贬窜江湖。故自称幽人。
⑤栖(qi):鸟类歇宿。
⑤寂寞沙洲冷:一作“枫落吴江冷”。沙洲:江河中由泥沙淤积而成的小块陆地。
【评析】
这首《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是苏词的名篇之一。关于这首词的编年,王文诰《苏诗总案》定为元丰五年十二月,以后很多注本都沿用此说,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因为苏轼寓居定惠院,是初到黄州时的事情。据宋傅藻的《东坡纪年录》、王文诰的《苏诗总案》等记载,苏轼元丰三年二月一日到黄州,寓居定惠院;五月家属到黄,即迁居临皋亭,以后便不再有“寓居定惠院”的记录。所以苏轼写作此词,只能在元丰三年二月到五月这一段时间,而不会是元丰五年的十二月。另外,从此词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上看,也极像初贬黄州时期的作品。如词中使用的“幽人”这个词,在元丰三年初的诗作中就多次见到(《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幽人无事不出门”;《石芝》:“幽人睡息来初匀”等),而在元丰五年十二月前后却绝不见使用。所以此词作于元丰三年当无疑问。据我个人的推断,具体时间为二月底或三月初,这在后面还要论及。
关于这首词的写作主旨,前人曾有过一场十分热烈的争论。概括起来,大概可以归纳为三类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此词是为某一女子而作。如宋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即说:“东坡先生谪居黄州,作《卜算子》云……其属意盖为王氏女子也,读者不能解。张右史文潜继贬黄州,访潘邠老尝得其详,题诗以志之……”云云。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四曾引吴曾此说,但却又提出新解,“……谓此词东坡在惠州白鹤观所作,非黄州也。惠有温都监女颇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闻东坡至,喜谓人曰:‘此吾婿也。’每夜闻坡讽咏,则徘徊窗外。坡觉而推窗,则其女逾墙而去。坡从而物色之,温具言其然,坡曰:‘吾当呼王郎与子为姻’。未几,坡过海,此议不谐。其女遂卒,葬于沙滩之侧。坡回惠日,女已死矣,怅然为赋此词……”后来沈雄在《古今词话》中坚主此说,而龙辅《女红余志》、邓廷桢《双砚斋词话》则认为这是“以俗情附会”,决不可信。今天我们看这种说法,觉得确属小说家的编造杜撰,这是没有疑问的。这大概也反映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既然苏轼所作为婉约一类,人们便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倚红偎翠”的内容,想从这方面寻出些写作的缘由,这也可谓“事出有因”吧!
第二种意见认为此词是一首政治诗,有非常具体的影射内容。如《类编草堂诗余》卷一引宋代鲖阳居士语:“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考槃》是《诗经·卫风》中的一篇,《毛诗序》认为其诗系刺卫庄公“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后来张惠言(《词选》)、谭献(《复堂词话》)赞同此说,(如谭献就认为“……此亦鄙人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而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篇》)、王士禛(《花草蒙拾》)、王国维(《人间词话》)等则力辩其非,王士禛甚至说鲖阳居士是“村夫子强作解事,令人欲呕。”观点是针锋相对的。我们认为,注意作品的思想内容,当然是好的,但如果割裂了艺术形象,断章取义,甚至字笺句解、穿凿附会,像鲖阳居士这样捕风捉影地曲解前作,那就完全不可取了。
第三类意见,认为此词是以鸿雁自寓感慨。如清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云:“此亦有所感触,不必附会温都监女故事,自成馨逸。”黄蓼园在《蓼园词选》中也说:“按此词乃东坡自写在黄州之寂寞耳。初从人说起,言如孤鸿之冷落;第二阕专就鸿说,语语双关,格奇而语隽,斯为超诣神品。”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
苏轼这首词,显然不是写风流韵事的。词中的“幽人”、“惊起”、“有恨”等字面,都明显地与情事无关。事实上,作者在这首词中,是在寄托人生的感触,表达自己贬谪黄州后孤独寂寞,却又傲岸不屈、孤芳自赏的情怀。由于作者采用了托物起兴的手法,“依微以拟议”、“婉而成章”(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所以显得用意隐微,不容易直接看出。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寻绎,作者的寄托还是不难发现的。
起首二句:“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其中的“缺”、“疏”、“断”等几个字,有人认为是“极写幽独凄清的心境”,有道理,但是不全面。我认为这里还包含着实写的意义。“缺月”,指上弦月或下弦月,表示时间是月初或月末。“疏桐”,指没有或很少花叶的梧桐,据《逸周书·时训解》记七十二候,则“清明之日,桐始华”,而四月桐叶乃长,所以“疏桐”所表示的时间,大概是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不会更晚。从词的下文中“寒枝”、“沙洲冷”等语来看,这个推断大致是不会错的。
这是一个寂静、寒冷的春夜,弯弯的月亮挂在天边,透过梧桐的扶疏的枝叶,洒下清冷的光辉。夜渐渐地深了,白日的喧嚣已经逐渐停止,于是四周便只有死一般的沉寂。诗人在一开始为我们描绘出这样一幅凄清冷寂的春夜图景,实际上,是为了渲染一种环境、一种气氛,并以此为背景,来引出“幽人”的活动。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在这个寒冷、寂寞的漫漫长夜里,诗人孑然一身,踽踽而行,孤独地徘徊在天地之间。没有人想到他,更没有人理解他。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生命与他为伴的话,那就是在夜空中悲哀地鸣叫着飞过的一只失群的孤雁。他们相同的命运,更加强烈地触发了诗人此时此刻的无限孤独之感。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受到统治者的打击迫害之后,窜逐江湖,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他们内心的孤独和悲凉是可想而知的。屈原《涉江》云:“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王粲《登楼赋》中有“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之句。柳宗元的绝句《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都是写茫茫的天地、空旷的宇宙,在这个冷漠的背景上,展示一个孤独的抗世者的形象。苏轼笔下的寒冷的春夜,与此具有相同的意义。所不同的,是苏轼眼前毕竟还有一只孤鸿,还可以得到一丝慰藉。这就难怪诗人要把它当作天涯知己,在孤鸿的身上寄托自己痛苦的人生感触了。这是此词自然过渡到下片的内在的逻辑,有人指出此词上片“言鸿见人”,下片则“言人见鸿”,那仅仅是表面上的联系而已。
词的下片,从字面上看,是“专就鸿说”,实际上却是“语语双关”(黄蓼园语)。“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这两句似乎是写鸿雁逃脱矰弋罗网之后的惊惧,然而同时,又何尝不是诗人对“乌台诗案”痛楚往事的咀嚼和回顾!这里有身陷囹圄的心头余悸,也有逐客楚囚的满腔悲愤(苏轼赴黄途中,多次提到自己是“逐客”、“楚囚”,如“未忍悲歌学楚囚”、“夫子自逐客,尚能哀楚囚”、“逐客不妨员外置”,等等)。然而举目茫茫,谁可告语?诗人只有借孤鸿的形象,来寄托内心的痛苦、来影现自己罢了。这种手法,就是托物寄言的所谓“兴”体。刘勰曾指出:“比显而兴隐”(《文心雕龙·比兴》),托物寄言,物是描写的主体,思想感情只是婉转微妙地寄托于物中,所以是隐微的,不容易看出。这是“兴”体的一个特点,也是此词构思上的重要特征,黄蓼园认为此词“格奇而语隽”,主要大概就是从这里着眼的。
最后两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是对孤鸿的栖止更具体、更生动的描述,同时也是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来展示诗人的内心世界。这里的“不肯栖”三个字,过去曾被人讥为“语病”,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拣尽寒枝不肯栖’之句,或云鸿雁未尝栖宿树枝,唯在田野苇丛间,此亦语病也。”对此,王楙反驳说:“仆谓人读书不多,不可妄议前辈词句。观隋李元操《鸣雁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飞空井傍。’坡语岂无自耶!”(《野客丛书》)争论的内容,仍然集中在鸿雁是否栖宿树枝的问题上,其实这都不是苏轼所关心的。苏轼在这里着意表现的,是“不肯”栖——这是一种选择、一种姿态。梧桐向来被认为是“高洁”的树,只有凤凰鹓雏之类才栖止其上,但苏轼笔下的这只孤鸿,却宁愿歇宿在卑湿的沙洲,而“不肯”栖止于梧桐的“寒枝”上,它自有怀抱、自有追求,决不屈从于尘俗的价值观念,而是特立独行——这正是诗人的托意所在!通过这只孤鸿的形象,诗人抒发了自己虽遭贬谪却傲岸不屈,远离尘俗而自甘寂寞,孤芳自赏、孤标傲世的操守和情怀,抑郁悲愤之心、孤洁清高之气,一寄之于鸿。使词中咏物和抒怀这一明一暗的两条线索,至此得以浑然归结。而“寂寞沙洲冷”一句尤其照应“黄州定惠院寓居”这个题目,使得全词从构思上得以完整地收束。
这首《卜算子》是苏轼词中的名篇,曾经受到前人很高的评价。如黄庭坚曾说此词“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山谷题跋》)那么,“语意高妙”,究竟“高妙”在哪里?“无尘俗气”,又该怎样理解呢?清代的刘熙载在《艺概》卷四中评黄庭坚此语时,有一段案语,对我们是有启发的。他说:“余案:词之大要,不外厚而清。厚,包诸所有,清,空诸所有也。”所谓“包诸所有”,就是指生活的积累、感情的蕴蓄深厚。乌台诗案使苏轼从统治阶级的上层一变而为阶下囚,而且险遭杀身之祸,这种遭遇,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发生深刻的变化,他对统治阶级有了重新的认识,对生活有了新的、更深刻的理解,沉痛、悲愤、抑郁、苦闷,而又傲岸不屈、孤芳自赏,这种种感情郁勃盘旋于其胸中,这就必然使得此词具有极大的感情浓度。这就是所谓“厚”,所谓“包诸所有”。但同时,作者在表达自己的这种复杂、深沉的感情的时候,却又注意了艺术的形象性,他在词中似乎句句是在说鸿,人的影子完全融化在鸿的形象之中,通过描写鸿雁的凄清、幽寂、孤独和高洁的形象,来隐约地透露出自己的情怀。鸿雁的形象塑造得愈真实、愈完整,人的寄托愈是不留痕迹、具有的渗透性愈强,则词的艺术性就愈高,也就愈加达到了刘熙载所说的“空诸所有”的境界。清人周济论词,主张“有寄托入,无寄托出”,与刘熙载的“包诸所有、空诸所有”的理论实质上是一样的。
苏轼的这首词在内容上也很有特色。过去很多人以为此词前半写景,后半咏物,不同于一般词前片写景,后片必抒情的旧格,于是便大加称赏。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此词本咏夜景,至换头但只说鸿,正如《贺新郎》词‘乳燕飞华屋’,本咏夏景,至换头但只说榴花。盖其文章之妙,语意到处即为之,不可限以绳墨也。”元代的吴师道在《吴礼部词话》“东坡贺新郎词”一条中也说:“东坡《贺新郎》词‘乳燕飞华屋’云云,后段‘石榴半吐红巾蹙’以下皆咏榴;《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云云,‘缈缥孤鸿影’以下皆说鸿,别一格也。”等等。从字面的内容上看,确实是这样的。但“语意到处即为之”,却并不等于作者行文洒脱,随意而驻,它反映的恰恰是此词构思上的精巧,是作者艺术腕力的高超。另外,换头之后,也并非“但只说鸿”,而是“语语双关”,是诗人的借物寓言、自抒怀抱。从这一层意思上看,此词前片是景语,后片仍然可以看作是情语。吴师道认为此词“别一格也”,不过是着眼于字面的内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