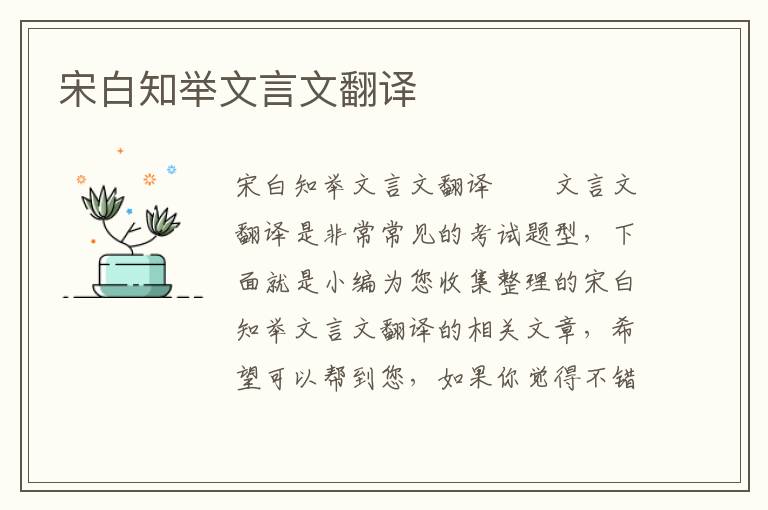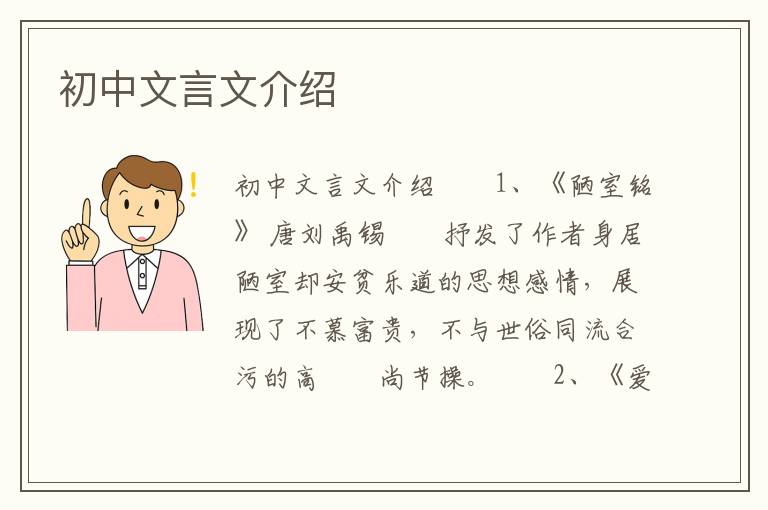【简介】感谢网友“雕龙文库”参与投稿,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方便大家学习。
燕瘦环肥谁敢嗔
文学史上同一个时期的诗歌园地,往往是姹紫妍红,争奇斗艳,形成不同的风格和流派。如果我们不能同时欣赏各种风格、流派诗歌的佳妙,也就不能正确地欣赏其中一种风格、流派诗歌的佳妙;如果我们不能辨认各流派作家的艺术特色,也就很难真正把握某一作家的特色。这里,展开横向比较尤有必要。
“诗中有画”一辞,本来是苏轼用以评价王维诗歌特色的评语,但它一度在古代诗词批评中用得太滥,似乎只要某诗形象性较强,或用了一二颜色的字面,线与形的字汇,都可奖以此语。其实这事并不那么简单。作为画家兼诗人的苏轼,对于画家兼诗人的王维的诗的特色是确有领悟的。诗和画本来是有区别的两门艺术,借莱辛《拉奥孔》极精辟的论断来说:“绘画凭借线条和颜色,描绘那些同时并存于空间的物体;诗通过语言和声音,叙述那持续于时间上的动作。”而自称“前身应是画师”的王维,是有意识地将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原则用于作诗。这特点,通过与同时诗人的比较更能清楚地看出。差异太大的诗人或诗篇作比较,效果较小;题材诗风接近的诗人或诗篇相比较,则易猎微穷精,人们不是常将孟浩然与王维并称么?孟浩然《春晓》诗不是也曾被人轻许以“诗中有画”么?不妨就以二人为例谈起: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孟浩然《春晓》)
桃红复合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僮未扫,莺啼山客犹眠。(王维《田园乐》)
王维《田园乐》写的是春晓之景、有春眠之事,又提到“宿雨”、“花落”、“莺啼”等等,这些都与孟浩然《春晓》诗一一吻合。但这两位诗人在表现手法上却大有差异,这种差异也反映在他们别的作品上,是值得注意的。扼要地说,孟浩然《春晓》从春眠不觉晓写到闻啼鸟而惊梦,又写到酒醒后对夜来风雨的回忆,从而引起惜花的心情。全诗展示了一个有序的时间过程,即莱辛所说的“持续在时间上的动作”(可以包括心理的活动),却没有涉及多少空间的显现。所以它更是本色的诗的手法。王维《田园乐》可不同了,桃红带雨、柳绿含烟、满地落花、空中莺啼,都是在“山客犹眠”的那一时刻“同时并列于空间的物体”。按莱辛的标准,这正是绘画的手法。所以,尽管孟浩然诗也富于形象性,却不能叫“诗中有画”,而王维诗则当之无愧。这种比较还可以继续进行: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王维《渭川田家》)
孟浩然《过故人庄》四联可以概括为应邀赴宴、途中所见、开筵谈心、殷勤话别,就“过故人庄”情事一一写来,展示着“持续在时间上的动作”,这是诗。王维《谓川田家》则是写黄昏时分散见在村落阡陌上的各种情景:牛羊归巷、老农候门、雉雊蚕眠、田夫闲话等等,彼此并无时间延续关系,全诗就象电影的镜头一一摇过,着重在空间显现。这是诗中画。再看两组诗句: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孟浩然《夏夕南亭怀辛大》)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
虽然都写暮色落日景象,孟浩然句用“忽”、“渐”等时间副词,仍重时间叙述。王维句用“直”、“圆”等形状线条字面,仍重空间显现。难怪香菱读此二句“合上书一想,倒象是见了这景的”(《红楼梦》)四十八回)。
以上比较,说明偏重于空间的显现是“诗中有画”的一个重要特征,却并不等于说“诗中有画”的涵义就仅此而已,因为苏东坡当初给王维诗下评语时只是凭着一种艺术敏感与直觉,并非精确的定义,也并不等于说“诗中有画”就一定好。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的方面转化的。
前人论填词结句有这样的论点:“或以动荡见奇,或以迷离称隽,着一实语败矣。”这种论点不只可以用来检验诗词关于物象或行动的描绘。不论是“日出江花红胜火”还是“山寺月中寻桂子”,尽管都是有画的,但这种画面写得并不沾滞,没有受物象或行动的种种偶然性细节的束缚……更重要的是表现了诗人对特定的自然景色的爱恋和怀念。……倘若以画译词,不仅难于把“何日更重游”的心境画得象诗句自身那么明确,而且在“郡亭枕上看潮头”或“山寺月中寻桂子”的诗人白居易的精神生活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可能被视觉感受中的各种特征所冲淡。(王朝闻《从白居易<忆江南>说开去》)
我们据此以比较王维《田园乐》和孟浩然《春晓》,就会发现“桃红”、“柳绿”二句不免沾滞,缺乏新鲜的启示,至后二句才渐入佳境;而“春眠不觉晓”的画面却流动着一股生意,启人妙思。所以《春晓》在艺术上反高一筹。
下面举盛唐三大诗人江行五律各一首: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李白《渡荆门送别》)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远,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王维《汉江临泛》)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杜甫《旅夜抒怀》)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短短十个字就写了多少景物!好象夜空下整个的宇宙都囊括在这两句诗中了。如果对照一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这里同样是上对天空下临江面的景色,而四句实际相当杜诗中的两句。其爽朗不同于杜诗的凝重是一目了然的。”(林庚)而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则又是用极省净而入微的笔触,画出的山水平远的图景。同类诗句还有“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终南山》)它所妙达的色、空关系,深契禅机,又与李杜异趣。
由此我们又想到中晚唐擅长爱情诗的三位高手,即刘禹锡、元稹、李商隐。他们各有千秋,不比较不能尽其妙。相形之下,刘禹锡有别于两家的最大特点是拟民歌,而非文人抒情诗。换言之,诗中抒情主人公不等于作者自己: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竹枝词》)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竹枝词》)
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联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踏歌词》)
这些诗具有桑间濮上之音和劳动生活情调。“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竹枝词》),绝类“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浇水来我灌园”的意味;“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的对歌情景,“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的狂欢舞会,均能反映巴楚民俗。他写民间少女的初恋与失恋,没有纤细柔弱的伤感,具有轻快乐观的情调。这是文人抒情诗不具备的特色。
元稹诗则表现个人生活情感。他的情诗写作于晚年,多恋旧、悼亡、伤逝及忏悔的情绪: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春晓》
检得旧书三四纸,高低阔狭初成行。自言并食寻常事,唯念山深驿路长。(《六年春遣怀》)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遣悲怀》)
他的写法是通过具体情事的白描,以真实的细节感人。《遣悲怀》忆贫贱时夫妻好合,精神反多慰藉;今日虽富贵,而夫妻生死异路,转觉空虚,何以为情。“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语言朴素,情事感人,正是新乐府作者本色。
李商隐诗虽亦自抒情感,但全不见具体的情事,只是专工情绪的发抒,扑朔迷离,近于词境,有“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之感。诗中表达一种执着的相思,多近单恋的情结: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堂外有轻雷。金蟾齧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
刘禹锡诗语具民歌风,元稹诗语较生活化,李商隐诗的语言刚典丽精工,是高度文学化的。其诗歌意象具有朦胧色彩,诗中对仗或结联多透骨情语。皆警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等等,或寓希冀,或示执着,最能见李商隐爱情诗之特色。
诗词风格大较在一庄一媚,前人论填词有“娇女步春”之喻。然而就在晚唐五代文人词中也具有不同的风格或个性。虽然我们不能对其妄加轩轾,但通过比较辨析,区别环肥燕瘦,对于作品的品鉴分析,无疑是大有益处的。如温庭筠、韦庄、李煜这些分别代表着晚唐、西蜀,南唐词风转变的里程碑式的作家,关于他们的区别,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有一精到的比譬:“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温庭筠),严妆也;端己(韦庄),淡妆也;后主(李煜),则粗服乱头矣。”这比较不但使我们看到了三家词的不同意境(或意象)美,而且还可以领略到一条通向北宋晏欧诸公的令词发展道路,即从歌筵之词到抒情之作的渐洗铅华的发展趋势。周济对温、韦等词人的比较尚停留在风格上,夏承焘则从具体表现手法上,对温韦二家作了更细致的比较,指出“温词较密,韦词较疏;温词较隐,韦词较显。”(《论韦庄词》)试看两家代表作:
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 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凤。(温庭筠《菩萨蛮》)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炉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韦庄《菩萨蛮》)
温词的上片写出了两个人物和两种环境:上两句写居者及其环境的舒适温暖;下两句写行者及其环境的凄清寂寞。四句中说了几层意思。韦词通首只一层意思,说游人到了江南,不愿还乡乃是因为故乡难还。前人论文有“密不容针”、“疏可走马”的说法。正可以用来形容温韦词的上述区别。再者,温词通过居、行双方环境的对照,自然流出怨别伤离情绪,却未著“愁”、“恨”等情感字面。而韦词的词意则表现得十分明快。由此可见二者的隐、显之别。在比较中点明韦庄疏、显的特色后,夏先生从而肯定“把当时文人词带回到民间作品的抒情道路上来;又对民间抒情词给以艺术的加工和提高。这是他在词的发展史上最大的功绩。”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比较可以从不同角度和层次上进行,无论在作品欣赏和作家评论都是不可忽略的方法。
生活中固不能排斥类似的情景,而诗人有时也会有某种相同(或正好相反)的体验。所以在古人诗词中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之笔,而它们确非彼此承袭,又不能完全替代。姑称之为“诗词类语”。参照比较读之,往往能使读者品鉴入微。
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
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
同样写情亲间阔别重逢,前者是自幼分离,及长邂逅相遇,不敢贸然相认,才有“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的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后者是故人之别,猝然相逢,惊喜之余,感到各自老了几分,却不致于相见不相识。
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常建《三日寻李九庄》)
桃花竟日随流水,洞在青溪何处边? (张旭《桃花矶》)
都用桃源典故写景,前者以直叙作结,见兴会淋漓之情;后者以问语作结,多摇曳不尽之致,机抒虽同,风趣各异。有语同而情异者,如“人生何处不离群”(李商隐)强调生别之愁,“人生何处不相逢”(杜牧)则强调知遇之乐。正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有情同而语异者,如“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以恳切动人,“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以豪迈感人,均传送别之深情。他如:
道是无情却有情(刘禹锡)
多情却似总无情(杜牧)
相见时难别亦难(李商隐)
别时容易见时难(李煜)
书被催成墨未浓(李商隐)
满纸春心墨未干(王实甫)
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顾复)
但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李之仪)
等等。读者在欣赏中如能留意诗词类语的比勘揣摸,必能于诗意有深细的理解与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