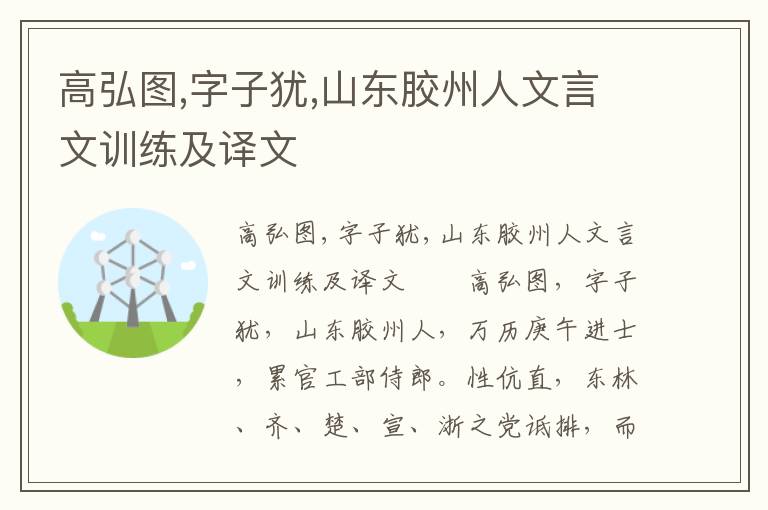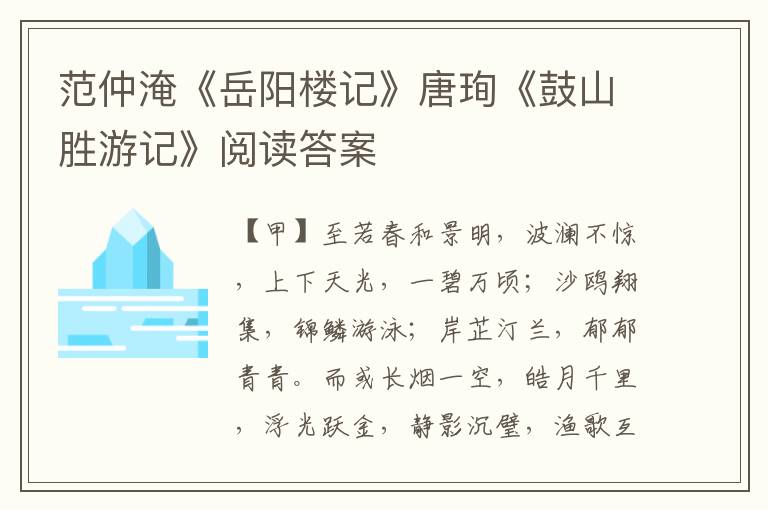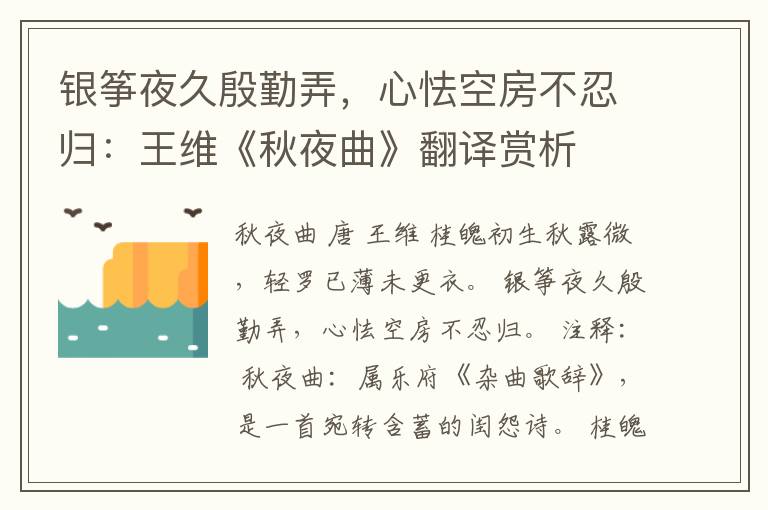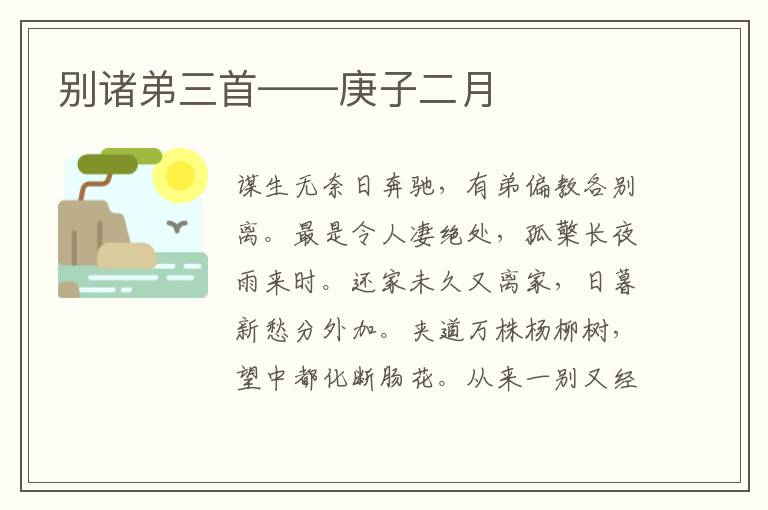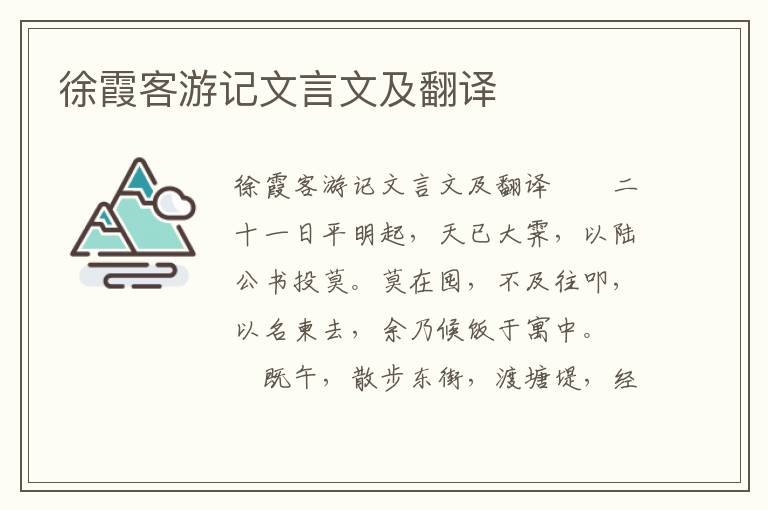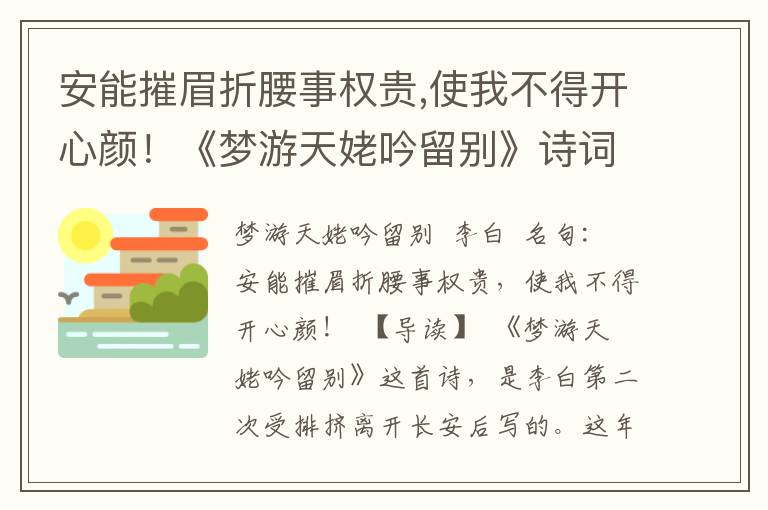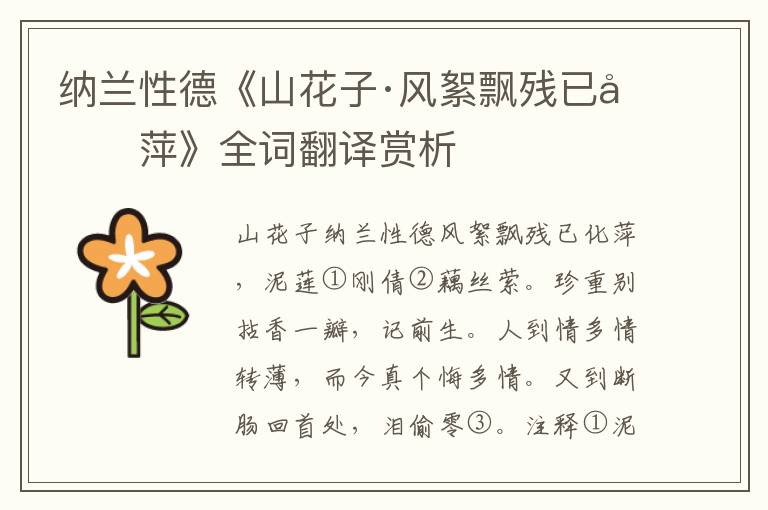【简介】感谢网友“雕龙文库”参与投稿,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方便大家学习。
李商隐在诗史上的贡献
唐代诗歌经过盛唐和中唐充分开拓后已难乎为继,晚唐一般诗人的作品创造性不大,题材、境界较为狭小。但也有一二例外,这便是李商隐和杜牧的诗歌创作。尤其是李商隐,他在对中唐已经开始上升的爱情与绮艳题材的开拓、在向心灵世界深入等方面,把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卓然成为大家。
一、李商隐的生平与诗歌内容
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从祖父起,迁居郑州。父亲李嗣曾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县令。商隐三岁时,父亲受聘为浙东(后转浙西)观察使幕僚。他随父由获嘉至江浙度过童年时代。李家从商隐曾祖父起,父系中一连几代都过早病故。商隐十岁,父亲卒于幕府。孤儿寡母扶丧北回郑州,“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姊文》),虽在故乡,却情同外来的逃荒者。这种孤苦不幸,使他较早体验到了人世的艰辛,同时也促使他谋求通过科举,振兴家道。在“悬头苦学”中获得高度的文化艺术修养,锻炼了他执着的追求精神。
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商隐谒令狐楚,受到赏识。令狐楚将他聘入幕府,亲自指点,教写今体文。楚子令狐绹又在开成二年(837)帮助他中进士。但就在这一年底,令狐楚病逝。李商隐于次年春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王茂元爱商隐之才,将最小的女儿嫁给他。当时朋党斗争激烈,令狐父子为牛党要员,王茂元被视为亲近李党的武人。李商隐转依王茂元,在牛党眼里是“背恩”的行为,从此为令狐绹所不满。党人的成见,加以李商隐个性孤介,他一直沉沦下僚,在朝廷仅任九品的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和闲冷的六品太学博士。为时都很短。从大和三年踏入仕途,到大中十二年去世,三十年中有二十年辗转于各处幕府。东到兖州,北到泾州,南到桂林,西到梓州,远离家室,飘泊异地。他最后一次赴梓州作长达五年的幕职之前,妻子王氏又不幸病故,子女寄居长安,更加重了精神痛苦。时世、家世、身世,从各方面促成了李商隐易于感伤的、内向型的性格与心态。他所秉赋的才情,他的悲剧性和内向型的性格,使他灵心善感,而且感情异常丰富细腻。国事家事、春去秋来、人情世态,以及与朋友、与异性的交往,均能引发他丰富的感情活动。“庾信生多感,杨朱死有情”(《送千牛李将军》),“多感”、“有情”,及其所带有的悲剧色彩,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李商隐童年时代受业于一位精通五经、恪守儒家忠孝之道的堂叔,十五六岁时曾在玉阳山学道。晚年,“丧失家道,郁郁不乐”,借佛理解脱烦恼,思想中儒佛道的成分兼而有之。他有“匡国”用世之心,也有过“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的出世念头。他重视自身的价值与创造,《上崔华州书》云:
始闻长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耶?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是以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
他反对机械复古,认为道并非周、孔所独能,自己和周、孔都体现着道。为文不必援经据典,不必忌讳,应挥笔独创,不甘居古人之下。从这种颇具锋芒的议论中,可见其思想的自主与自信。
李商隐是关心现实和国家命运的诗人,他的直接反映时事政治的诗,借古喻今的咏史诗,以及少数,在其现存的约六百首诗中,占了六分之一。著名的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一开头就展示了京西郊区“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的荒凉残破景象。接着,借村民口诉,展示社会症结。长诗体势磅礴,既有唐王朝衰落历史过程的纵向追溯,亦有各种社会危机的横向解剖,构成长达百馀年的社会历史画卷。藩镇的割据叛乱,宦官的专权残暴,边患的严重威胁,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赋税的苛重,人民生活的穷困,治安的混乱,财政的危机,等等,都在长诗中得到揭示,而这些方面,李商隐在其他一些诗中也一再予以关注。
文宗大和九年(835)冬,甘露事变发生,李商隐于次年写了《有感二首》、《重有感》、《曲江》等诗,抨击宦官篡权乱政,滥杀无辜,表现了对唐王朝命运的忧虑。当时慑于宦官的气焰,包括白居易、杜牧等诗人在内,还没有谁能像李商隐这样写出有胆识的作品。李商隐的朋友刘蕡,因反对宦官而被贬死。他在酬赠、哭吊刘蕡诗中,反复为刘蕡鸣不平:“江风吹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蕡》)“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哭刘蕡》)把刘蕡蒙冤贬死的遭遇,放在政局动荡、宦官肆虐、皇帝昏聩的政治环境下加以描写,同时把比兴象征手法引入以现实政治为题材的作品中。
李商隐反对藩镇破坏国家统一。一方面他赞成朝廷对藩镇用兵,歌颂在平叛中立功的将相;另一方面,对于朝廷存在的问题,他也尖锐批评。如针对伐叛中暴露的军政腐败现象,追究根源,认为关键在于宰辅不得其人。将反对藩镇割据和批判朝政结合起来,在思想深度上超出以前的同类作品。
李商隐的咏史诗历来受到推重,而从内容上看,则绝大部分属于借咏史以讽时的政治诗。如《隋宫》: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写隋炀帝的逸游和荒淫,从已然推想到未然,从生前预拟死后,在含蓄委婉的抒情中,昭示历史教训,寓含对当代统治者的警戒讽刺。
唐代后期,许多皇帝不重求贤重求仙,希企长生。李商隐借咏史一再予以冷嘲热讽。《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借贾谊宣室夜召一事,加以发挥,慨叹贤才被视同巫祝,讽刺皇帝不顾苍生,但信鬼神。《瑶池》:“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在传说的基础上虚构出西王母盼不到周穆王重来的场景,含意深长地说明了求仙无益,神仙也不能使遇仙者免于死亡。
安史乱后,唐王朝由极盛走向衰败,李商隐对玄宗的失政特别感到痛心,他的一些相关咏史之作,讽刺也特别尖锐。如《马嵬》: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诗中每一联都包含鲜明的对照,再辅以虚字的抑扬,在冷讽的同时,寓有深沉的感慨。他的《龙池》诗更为尖锐地揭露玄宗霸占儿媳的丑行,连本朝皇帝也不留情面,不稍讳饰。
除政治抒情诗外,李商隐诗集中更多的是吟咏怀抱、感慨身世,以及有关男女爱情的作品。其中一些咏怀诗表现了他的用世精神。如“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希望做一番扭转乾坤的大事业,然后归隐江湖。“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城上》),借历史人物喻自己的才能抱负和追求。但无论怎样执着,生逢末世,现实总是不断让他感到抱负成虚。“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有感》),实际上是有才无命,命薄运厄,在个人命运背后,有社会时运。“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天涯》),以“最高花”自喻,慨叹时代之黯淡没落和自身之沦落。正因为生性多情善感,而一生又是“沦贱艰虞多”(《安平公诗》),所以李商隐诗大量抒发的是一种人生感慨。它基于诗人自我体验,但又往往反映了世人对命运遭际、人情世态种种带有普遍性的体验。
除在直接写怀抱身世诗中抒发人生感慨外,李商隐的咏物诗也多托物寓慨。如:“流莺漂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流莺》)借流莺漂荡流转,伤己之无所依托,于轻倩流美中寓凄惋之思。而与《流莺》寓感相近的《蝉》诗则出语愤激:“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慨叹蝉悲鸣传恨,欲断仍嘶,却无人同情。诗人写蝉即以自寓,达到人与物一体的境界,抒写了羁宦漂泊,举目无亲的人生与世情感慨。
李商隐抒情之作中,最为杰出的是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这些诗是李商隐诗歌独特的艺术风貌的代表。以其深情绵邈与艺术独创性,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古代不少爱情诗的作者,往往以一种玩赏的态度来对待女子及其爱情生活。李商隐的爱情观和女性观是比较进步的,他以一种平等的态度,从一种纯情的而不是色欲的角度来写爱情、写女性。他曾在《别令狐拾遗书》中对女子被深闭幽闺缺乏婚姻自主权,寄以极大的同情。他的爱情诗,情挚意真,深厚缠绵。如《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一开头就说尽了离情别恨。颔联春蚕蜡炬,到死成灰。比喻中寓象征,至情至性,已经超越爱情而具有执着人生的永恒意义。颈联于细意体贴关注中见两心眷眷,两情依依。末联是近乎无望中的希望,更见情之深挚。他把爱情纯化、升华得如此纯净而又缠绵悱恻,在古代诗歌中是罕见的。李商隐还写了“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无题》),那种被“贮之幽房密寝”,无权过问自己婚事的怀春女子;写了“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二首》其一),那种显然难得结合,却已经目成心许的爱情;写了那种终生难忘,遭受间阻,而又无法排遣、不易言说的恋情。这些描写,都或多或少有悖于封建礼教对于女性和爱情的态度,并往往在爱情体验中融入身世之感。
李商隐以他的诗,表现了美好的理想、情操,表现了人性中纯正、高尚的一面;同时,也曲折地显现了他那个时代政治环境气氛与士人的精神面貌。
二、朦胧多义与对心灵世界的开拓
李商隐诗歌在艺术上具有多方面成就。名篇如《有感二首》(五排)典重沉郁;《韩碑》(七古)雄健高古;《筹笔驿》(七律)笔势顿挫;《骄儿诗》(五古)类似人物写生;《鄠杜马上念汉书》(五律)具有古诗排奡之笔势;《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七古)豪放健举中见感慨深沉,等等,都各具面貌,极见功力。但从诗史的演进角度看,他以近体律绝(主要是七律、七绝)写成的抒情诗,特别是无题诗,以及风格接近无题的《锦瑟》、《重过圣女祠》、《春雨》等篇,其艺术成就和创新意义,尤其值得重视。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类作品所产生的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李商隐之前,韩孟、元白两大诗派兴盛于中唐。到了晚唐,韩愈、白居易那一类诗歌的情感内容与士人的心态已逐渐隔膜,韩诗的怪奇而壮大、白诗的平易少含蓄的笔法,已不适用于表达纤细情感的需要。中唐后期,李贺的瑰丽诡谲,开启了晚唐重心灵、重自我的趋向。之后,诗歌创作中出现三种值得注意的走向:1.情爱和绮艳题材增长,齐梁声色又渐渐潜回唐代诗苑;2.追求细美幽约;3.重主观、重心灵世界的表现。三者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出来,又有其内在联系。李商隐正是受这一走向推动,在表现包括爱情体验在内的心灵世界方面作了重大开拓,同时创造了“绮密瑰妍”(敖器之《诗评》)的诗美。
李商隐的抒情诗,情调幽美。他致力于情思意绪的体验、把握与再现,用以状其情绪的多是一些精美之物。表达上又采取幽微隐约、迂回曲折的方式,不仅无题诗的情感是多层次的,就连其他一些诗,也常常一重情思套着一重情思,表现得幽深窈渺,如《春雨》:
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
为所爱者远去而“怅卧”、“寥落”、“意多违”的心境,是一层情思;进入寻访不遇,雨中独归情景之中,又是一层情思;设想对方远路上的悲凄,是一层情思;回到梦醒后的环境中来,感慨梦境依稀,又一层情思;然后是书信难达的惆怅。思绪往而复归,盘绕回旋。雨丝、灯影、珠箔等意象,美丽而又细薄迷蒙,加上情绪的暗淡迷惘,诗境遂显得凄美幽约。
朦胧与亲切可感。李商隐不像一般诗人,把情感内容的强度、深度、广度、状态等等,以可喻、可测、可比的方式,尽可能清晰地揭示出来。为了表现复杂矛盾甚至怅惘莫名的情绪,他善于把心灵中的朦胧图像,化为恍惚迷离的诗的意象。这些意象分明有某种象征意义,而究竟要象征什么,又难以猜测,由它们结构成诗,略去其中的逻辑关系的明确表述,遂形成如雾里看花的朦胧诗境,辞意飘渺难寻。如《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所呈现的,是似有而实无,虽实无而又分明可见的一个个意象:庄生梦蝶、杜鹃啼血、良玉生烟、沧海珠泪。这些意象所构成的不是一个有完整画面的境界,而是错综纠结于其间的怅惘、感伤、寂寞、向往、失望的情思,是弥漫着这些情思的心象。诗的境界超越时空限制,真与幻、古与今、心灵与外物之间也不再有界限存在。究竟写什么?只首尾两联隐约暗示是追忆华年所感,而传达所感的内容则是五个在逻辑上并无必然联系的象喻和用以贯串这五个象喻的迷惘感伤情绪。喻体本身不同程度地带有朦胧的性质,而本体又未出现,诗就自然构成多层次的朦胧境界,难以确解。
李商隐诗的朦胧,与亲切可感的情思意象常常统一在一起。读者尽管难以明了《锦瑟》诗的具体思想内容,但那可供神游的诗境,却很容易在脑子里浮现。所以《锦瑟》虽号称难懂,却又家喻户晓,广为传诵。《重过圣女祠》中的名句:“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写圣女“沦谪得归迟”的凄凉孤寂处境,境界幽缈朦胧,被认为“有不尽之意”(吕本中《紫薇诗话》)。荒山废祠,细雨如梦似幻,灵风似有而无的境界亲切可感,而那种似灵非灵,既带有朦胧希望,又显得虚无缥缈的情思意蕴,又引人遐想,似乎还暗示着什么,朦胧难以确认。
“无题”一类境界朦胧的诗歌,在内涵上往往具有多义性。一篇《锦瑟》,聚讼纷纭。多种笺解,似皆有可通。所谓“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反映了可供多方面体味和演绎的多义性的特点。
多义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本来很常见,比兴、象征、用典、暗示,情在言外,旨冥句中,都可以造成多义。但一种多义是易解可解的,一种多义则难解、不可确解。李商隐属于后者。前者往往表现为在一些意象中带象征意义或在表层意义下掩藏着深层意义,虽然多义,多属外延的扩展,层次的加深。而李商隐的多义,往往是给读者提供多种解读的可能,构成解读上的复义。多重意旨之间可以是比较接近的,也可能是差距很远的歧解。
多义性的成因来自多方面。从文字表述亦即语言符号层面看,李商隐诗的意象、典故,以及词语意象之间的联系组合方式,都有可能导致朦胧。诗歌意象,在一般诗人笔下,客观性较强,能以通常的方式去感知。李诗意象,多富非现实的色彩,诸如珠泪、玉烟、蓬山、青鸟、彩凤、灵犀、碧城、瑶台、灵风、梦雨,等等,均难以指实。这类意象,被李商隐心灵化了,是多种体验的复合。它们的产生,主要不是取自外部世界,而是源于内心,内涵远较一般意象复杂多变。
李诗大量用典。典故由于内涵的浓缩性等原因,如果用得好,能在有限的字句中,包含丰富的、多层次的内容。李商隐又擅长对典故的内涵加以增殖改造,用典的方式也别开生面。他往往不用原典的事理,而着眼于原典所传达或所喻示的情思韵味。“庄生晓梦迷蝴蝶”,原典不过借以阐发万物原无差别的齐物我的思想而已,李商隐却抛开原典的哲理思索,由原典生发的人生如梦引入一层浓重的迷惘感伤情思。“望帝春心托杜鹃”,也由原典之悲哀意蕴而引入伤春的感怆,这些典故不是用以表达某种具体明确的意义,而是借以传递情绪感受。对于读者,情绪感受所引发的联想和共鸣,可以是模糊朦胧、多种多样的。李商隐一生坎坷,对事物的矛盾和复杂性有充分的感受,结合他的体验和认识,常常把典事生发演化成与原故事相悖的势态,由正到反,正反对照,形成张力,把人思想活动的角度和空间大大扩展了。如《嫦娥》: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嫦娥得成月中仙子,本为常人所羡。李商隐设想嫦娥会因为天上孤寂而后悔偷吃了灵药。注家对诗旨猜测纷纷,说明这一典故经过反用之后,那种高远清寂之境和永恒的寂寞感,沟通了不同类型人物某种近似的心理,从而使诗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读。还有些典故,虽不是反用,但诗人作了别有会心的生发,如:“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梦泽》)从“歌舞能多少”方面寻问为迎合邀宠而节食减膳的效益,于是引发出“深慨宫中希宠美人的愚昧与麻木”等多种解说,以及“普天下揣摩逢世才人读此同声一哭”等联想,产生了多义性的效果。
李诗的多义性与词语意象组合也很有关系。诗人心理负荷沉重,精神内转,内心体验纤细敏感,当心灵受到外界某些触动时,会有形形色色的心象若隐若显地浮现。发而为诗,其意象往往错综跳跃,不受现实生活中时空与因果顺序限制。这种意象转换跳跃所造成的省略和间隔,导致读者在将其有序化的时候,见仁见智,产生歧义歧解。如《无题》:
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
意象和句子之间跳跃性都很大。诗人在追求不遂的迷茫失落之中,可能出现类似诗中的意乱情迷的心象与幻觉。云浆未饮,旋即成冰,是追求未遂的幻化之象。“如何”二句是与所追求的对象渺远难即之感。中间的跳跃变化,透露对方变幻莫测,难以追攀。这一切,可以是多种诱因(如爱情、交友、仕宦)导致的心事迷茫的感受。但究竟是何种诱因,读者在像蒙太奇一样闪烁变幻的意象面前,不能明确直接地得知,只能发挥各自的艺术联想,因而在解读时自然会出现多义。
李商隐诗歌多义性更为深层也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把心灵世界作为表现对象。李商隐许多诗歌所写的不只一时一事,乃是整个心境。种种情绪,互相牵连渗透,难辨难分。其心理状态,被以繁复的意象表现出来的时候,便无法明确地用某时、某地、某事诠释清楚。《锦瑟》诗开头即点出“无端五十弦”,可见意绪纷纭,决不是一时一事就能使作者陷入那样一种心境之中。以某种具体事件解之,不免挂一漏万,顾此失彼。《锦瑟》如此,无题诗也有类似现象。诗人表现的是萦绕于心间的一种莫名的愁绪,其来龙去脉自己都未必完全能清晰地理出头绪,诗也就加不上合适的题目而以“无题”名之。其中多数篇章只能看作是以爱情体验为中心的整个心境的体现。如《无题四首》其一: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全篇写“梦为远别”醒来后思念对方的心境。但那种殷切期待中只迎来“空言”和“绝踪”的失望,那种已隔蓬山,更复远离的间阻之感,作者除了爱情之外,在事业追求过程中和与朋友交往过程中,不都曾一次又一次地反复体验过吗?因此诗中所表现的那种交织着希望与失望的凄迷心境,也就并非单纯由爱情失意所引起。
李商隐有些诗,虽有一时一事的触动,但着力处仍然在于写心境。《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由登古原遥望夕阳触发,引起的是整个心灵的投注,百感茫茫,一时交集。诗中的情感,只有这“意不适”三字可以概括,而其原因和内涵,则几乎汇聚其毕生经历的感受和体验。
既然所表现的往往不限于具体情事,而是复杂的感情世界与多种人生体验,因而关于李商隐诗的种种歧解,便可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融合。沟通众说中某些合理成分,从诗境的多面性、多层次性着眼,或许更能接近原作。对于无题诗,一般读者可以不必根究其“本事”,而应通过把握其总体情感内涵,去领略其诗意与诗美。
三、凄艳浑融的风格
李商隐诗歌风格凄艳。艳,有来自六朝的文学渊源,但李商隐诗艳而不靡。在他那里,艳与爱情生活的不幸,身世遭遇的坎坷,乃至与对唐王朝命运的忧思相联系,表现出“哀感顽艳”的特色。
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其二)
已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无题二首》其一)
枫树夜猿愁自断,女萝山鬼语相邀。(《楚宫》)
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燕台诗四首·春》)
这些,都是把感伤情绪注入朦胧瑰丽的诗境,融多方面感触于沉博绝丽之中,形成凄艳之美。
李商隐诗不仅把凄与艳融合在一起,而且由凄艳通于浑融。李诗不重意象的外部联系,同时又多用美丽的辞藻与事典,这本来容易给人镶金嵌玉、支离饾饤的感觉,难得在这种形式中表现出深浑的大气候,但实际上李诗却是“沉博绝丽”(朱鹤龄语),绮艳而能浑融,在艺术上表现出博大的气象和完整性。这是由于:1.李商隐拥有自己的意象群。所用的意象在色调、气息、情意指向上有其一致性。2.李诗技法纯熟。声调的和谐、虚字的斡旋控驭,事典的巧妙组织,近体在形式上的整齐规范,都增加了诗脉的圆融畅适。3.情感的统一。那种孤独、飘零、惘然、无奈、寥落、伤感的情绪,浓郁而又深厚,弥漫在许多诗中,使诗的各部分得以融合、贯通,成为浑然一体。如《春雨》全篇浸沉在孤独枨触的情绪中,从这种情绪出发,借助于飘洒迷蒙的细雨融入迷茫的心境,依稀的梦境,以及红楼、灯影、云罗、孤雁等物象,诗境遂显得凄艳而浑融。短篇如《夜雨寄北》借思乡的愁绪,将此地与异地,现时与未来,实景与假想,巴山独对夜雨与剪烛聚首西窗等不同时地与场景,融合在一起。虽四句之间跳跃极大,但却是“水精如意玉连环”(何焯评语)的浑融境界。
李商隐所开创的风格和境界,是晚唐诗歌的重大收获,他总结前代诗歌艺术经验加以提高,同时在诗歌中吸取了骈文、赋、小说等文体的养分和技法,代表晚唐,而又高于晚唐。通过将李商隐和前代某些阶段诗歌与诗人对照,可以进一步看到他在创作上的取径和成就:
1.李商隐与齐、梁诗歌
李诗中爱情和绮艳题材比重很大,讲究词藻声律、对仗用典,这与齐、梁诗有渊源关系。但齐、梁诗主要兴趣在描写闺阁楼榭与女子的容貌体态服饰,重声色而乏性情。李商隐的爱情诗,侧重于感情领域的表现,摆脱了以满足感官欲望为特征的庸俗情调,以其深情绵邈把这一题材的诗境推向高峰。试看《无题二首》其一: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抒写对昨夜一夕相值、旋成间隔的意中人的深切怀想。在“身”不由自主的情况下,那种灵犀一点的心心相印,该是多么珍贵。突出了间隔中的契合、苦闷中的欣喜、寂寞中的慰藉。这与齐、梁诗把女子作为性爱赏玩的对象去写是不同的。
2.李商隐与阮籍
论诗歌的象征性和多义性,李商隐与魏晋之交的阮籍有相似之处。但在写法上,阮籍把复杂的心理导向玄思,以虚拟象征之意,隐约暗示诗旨。李商隐主情,心象与物象相融合,构成象喻,表现丰富复杂的情绪与心灵景观,显得更为真切生动。
3.李商隐与李贺
李贺写诗开始走向幽奥隐微的途径,对李商隐有直接先导作用。但李贺诗夹杂着生而未化的成分。李商隐精心结撰,才思绵密,既有沉郁之致,又精美妥帖。李贺所写的物象,往往具有特别的硬度和锋芒。又多用颜色字,瑰丽炫目。李商隐则是虽美艳而又较少给人色彩刺激,脱离了李贺的词诡调激,归于温润纯熟。
4.李商隐与杜甫
王安石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引)李商隐优秀诗歌所达到的浑融境界,在艺术上可以和杜甫诗歌的浑成境界遥相呼应。李诗之浑融,除上文所指出的意象、技法、情感等原因外,他之通于杜甫,更在于其诗“秾丽之中,时带沉郁”(施补华《岘佣说诗》)。李商隐跟杜甫一样,内心深处有一股郁结很深的沉潜之气,发而为诗,在情思的沉郁上十分相近。由于内在充实,通体完整,两人诗歌都达到了“浑”的境地。差异是,杜甫较李商隐外向,诗思经常盘旋在社会江山朝市之间,诗境与社会与自然直接沟通。“篇终接混茫”,所接的是外部世界。李商隐转向内心,内在浩浩茫茫,无涯无际,扑朔迷离,也有一种浑沦之状,成为唐诗中达于浑化层次的一种新境界。
李商隐给在盛唐和中唐已经有过充分发展的唐诗,以重大的推进,使其再次出现高峰。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心灵世界作出了前人未曾有过的深入开拓与表现。任何诗歌都这样那样地表现着心灵世界,李商隐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对心灵世界的丰富层次,它的变化的复杂奥妙,它的清晰的和不清晰的难以言说的领域,做了前所未有的细腻、传神的展示。围绕表现心灵世界,他在对于诗歌语言潜在能力的发掘,比兴象征手法和典故运用等方面,亦有许多独到的探索。
2.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艺术表现的领域:非逻辑的、跳跃的意象组合;朦胧情思与朦胧境界的创造;把诗境虚化。这样的非写实的艺术表现手法,不仅极大地扩大了诗的容量,且亦留给读者以更大的联想空间。
3.在无题诗、咏史诗、咏物诗三种类型诗歌的发展上做出重要贡献。他所创写的无题诗,在诗歌中成为一种富有特色的新体式。他的咏史诗,情韵深长,善于突破“史”的拘限,真正进入“诗”的领域,将咏史诗的创作,往更具典型性、抒情性的境界推进。他的咏物诗,托物寓怀,表现诗人独特的境遇命运、人生体验和精神意绪,在物与我、形与神、情与理等类关系处理上做出了新贡献。
4.在体裁方面,他的七律、七绝,深婉精丽,充分发挥了这两种诗体在抒写情感、表现心理方面的潜能。清代吴乔云:“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西昆发微序》)李商隐确实是继李白、杜甫、韩愈之后,再次为诗国开疆辟土的大家。
(本篇原载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