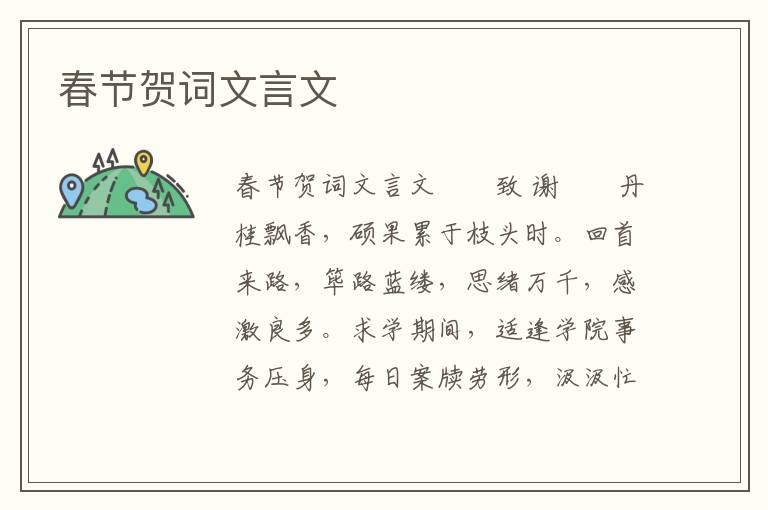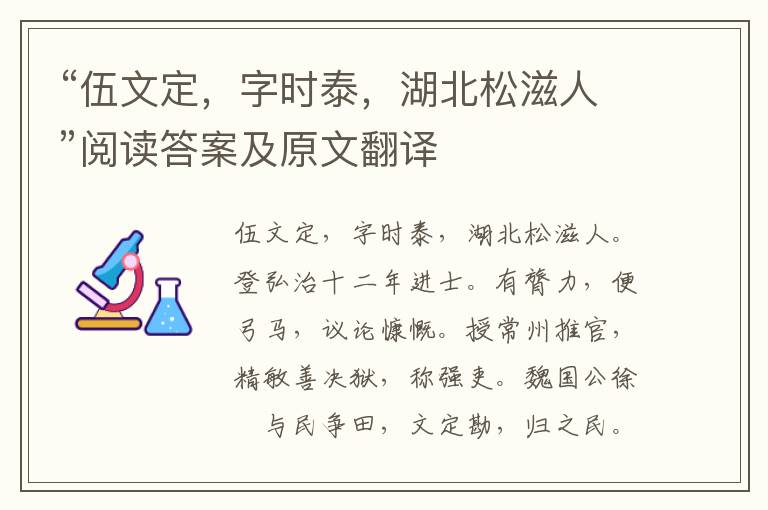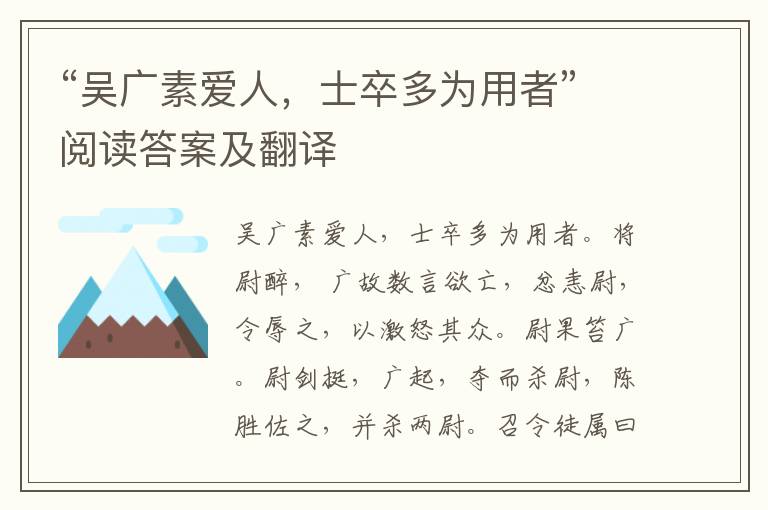【简介】感谢网友“雕龙文库”参与投稿,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方便大家学习。
唐代礼教松弛,士人行为放荡,刘禹锡也如此,不必以现代眼光来严格要求古人。题目所言刘之得妓与失妓,皆属传闻,未必有其事,我仅借此题,说明文献与真相之间的距离,指明文史考据之复杂。绮题惑众,愿承罪责。
刘禹锡之得妓,诞生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成语:司空见惯。关于此事,最早的记录有两处。一是孟启《本事诗》: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司空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倭鬌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
《太平广记》卷一七七转引时,“李司空”作“李绅”。岑仲勉《唐史馀沈》卷三认为“刘自和州追入,约大和元二年,至六年复出,于时绅方贬降居外,曾未作镇,何云罢镇在京”,“同时守司空者乃裴度,此涉于李绅之全误也”。卞孝萱作《李绅年谱》和《刘禹锡年谱》,逐年排比二人事迹,证定以李绅为李司空之不足凭据。然此属《太平广记》之误改李绅,并非《本事诗》原文。
二是范摅《云溪友议》卷中《中山诲》,颇多不同:
昔赴吴台,扬州大司马杜公鸿渐为余开宴。沉醉归驿亭,稍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我有也。乃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特令二乐伎侍寝。”且醉中之作,都不记忆。明旦修状启陈谢,杜公亦优容之,何施面目也。余以郎署州牧,轻忤三司,岂不过哉!诗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所叙更曲折,但破绽更明显。杜鸿渐是肃、代间名臣,卒于大历四年(769),在刘禹锡出生前三年。宋人刻意加以弥缝,如詹玠《唐宋遗史》即径改作“韦应物赴大司马杜鸿渐宴”,其实韦任苏州于杜去世后近二十年。
那么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呢?我在九年前曾撰文《司空见惯真相之揣测》(刊《新民晚报》2009年2月15日),认为《云溪友议》的叙述,很可能来自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韦是永贞革新间宰相韦执谊子,长庆间到夔州从刘禹锡问学,刘因故人子而无话不谈。三十多年后,韦回忆当年谈话撰成该书。事隔多年,不免有失实处。范摅撰《云溪友议》,更不免添加民间传闻,离事实尤远。至于真相,我推测“扬州大司马”是曾长期担任淮南节度使的名臣杜佑,刘曾担任他的掌书记七年,两人关系昵密,因而发生这样赠妓的非常事件。杜佑曾先后为司马、司空、司徒三司之职务,为司空见《旧唐书·德宗纪》记载,职衔为“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清宫使”,时在他从扬州入相之际,且为时较短即授司徒,其间刘禹锡一直随侍在他身边。当然其间也有难以解释的地方,即《云溪友议》称“昔赴吴台”,又称“以郎署州牧,轻忤三司”,刘诗也称“断尽苏州刺史肠”或“江南刺史肠”,刘任苏州刺史在大和五年(831),时杜佑去世已经十九年,显然难以契合。我认为在上举二书叙事中,包含了与刘禹锡生平有关的一系列细节,从招宴人来说,有扬州大司马杜公和李司空之别;从事发地点来说,有京师与扬州之不同;从刘禹锡的身份来说,有大和六年二月赴任苏州刺史和开成元年(836)自和州刺史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之不同。到底在哪个节点上传误,皆不可解,至今尚难以得到完美的解释。认为司空即杜佑,至少可以解释“扬州大司马杜公”曾任司空的身份,而“以郎署州牧,轻忤三司”,则可以刘贞元末至永贞间,以屯田员外郎助杜佑判度支盐铁,则郎及三司皆得落实。刘的出生,其实在当时属于苏州的嘉兴境内,颇怀疑此“昔赴吴台”不是指赴任苏州刺史,仅指他早年来往苏州、扬州间的一段经历。无论任苏州或和州刺史,都在韦绚从学刘禹锡以后,不可能见于二人间的谈话。拙解虽然还有一些疑问,但较前人自信得进一解。刘禹锡的谈话,经韦绚多年后回忆写出,再经范摅任意改写,几度变形,与事实不免出入,是可以理解的。
有得必有失。意外得妓与遇暴失妓,刘禹锡居然都碰到了。
《太平广记》卷二七三引《本事诗》载:“李丞相逢吉性强愎而沉猜多忌,好危人,略无怍色。既为居守,刘禹锡有妓甚丽,为众所知。李恃风望,恣行威福,分务朝官,取容不暇,一旦阴以计夺之。约曰:‘某日皇城中堂前致宴,应朝贤宠嬖,并请早赴境会。’稍可观瞩者,如期云集,敕阍吏先放刘家妓从门入,倾都惊异,无敢言者。刘计无所出,惶惑吞声。又翌日,与相善数人谒之,但相见如常,从容久之,并不言境会之所以然者。座中默然,相目而已。既罢,一揖而退。刘叹咤而归,无可奈何,遂愤懑而作四章,以拟《四愁》云尔。”居然又是李逢吉。《本事诗》是存留至今,至今无人疑其有伪,原文如下:“大和初,有为御史分务洛京者,子孙官显,隐其姓名。有妓善歌,时称尤物。时太尉李逢吉留守,闻之,请一见,特说延之,不敢辞,盛妆而往。李见之,命与众姬相面。李妓且四十余人,皆处其下。既入,不复出。顷之,李以疾辞,遂罢坐,信宿绝不复知。怨叹不能已,为诗两篇投献。明日见李,但含笑曰:‘大好诗。’遂绝。诗曰:‘三山不见海沉沉,岂有仙踪尚可寻。青鸟去时云路断,嫦娥归处月宫深。纱窗暗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料得此时天上月,只应偏照两人心。’欠一首。”两相比对,可以发现《太平广记》所引根本不是《本事诗》。虽然夺妓者都是李逢吉,且都说在他任东都留守期间,但差异太大,即《太平广记》说是刘禹锡,《本事诗》说子孙官显隐其名,刘的儿子官位、名声都未见超过啊!《太平广记》说是在皇城中堂设宴的众目睽睽之下夺妓,《本事诗》则仅为邀到家中相见;《太平广记》说作诗四章,《本事诗》则云“为诗两篇投献”。可以认为,《太平广记》所引书名有误,根据后面要引到的宋敏求的记录,可以确认《太平广记》的根据是另一部书《南楚新闻》。
这一故事之另一文本记录,则作唐末商人刘损事,记载最早见《灯下闲谈》卷上《神仙雪冤》:呂用之在维扬日,佐渤海王擅政,害物伤人,具载于《妖乱志》中,此不繁述。中和四年秋,有商人刘损,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扬州。用之凡遇公私往来,悉令损觇行止。刘妻裴氏有国色,用之以阴事构置,取其裴氏。刘下狱,献金百两免罪。虽即脱于非横,然亦愤惋。因成诗三首曰(诗略)。诗成,吟咏不辍。
此书下还有较详记载,写刘损在绝望之际遇一虬须老叟,仗侠而为刘夺还妻室,文长不录。《灯下闲谈》二卷,无作者名,通行有《适园丛书》本与《宋人小说》本,今人多以为宋人著,但就全书内容看,叙事所涉到后唐明宗时止,没有入宋后的痕迹,即很可能成于五代后期。此节所述渤海王,指乾符六年(879)到光启三年(887)以诸道兵马都统任淮南节度使的高骈,吕用之为其属吏,因蛊惑高骈崇信神仙事而擅权,《灯下闲谈》说时在中和四年(884),大体准确。问题在于《本事诗》有孟启自序,作于光启二年(886),时僖宗幸褒中,孟启本人大约也在京畿一带,从当时情况来说,两年间很难从淮南的刘损故事,流传到关中,成为另一个故事,换句话说,刘损的故事只不过是此组诗敷衍出来的夺妻故事的一个衍生情节,其形成过程大约经历了从光启间高骈、吕用之败亡到五代中期的漫长过程。上引文提到《妖乱志》,今人一般认为作者为诗人罗隐,我则一直有所怀疑,《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郭廷诲《广陵妖乱志》二卷”,郭廷诲则为后唐权臣郭崇韬之子,是刘损故事之完成宜在《妖乱志》成书以后。
关键还是要看所拟《四愁》诗的文本。这组诗的保存文本,追根溯源,有几种记载。一,《本事诗》所载“三山不见海沉沉”一首,作者缺名,记录时间为光启二年(886)。二,《灯下闲谈》录“宝钗分股合无缘”“鸾飞远树栖何处”“旧尝行处遍寻看”三首,作者刘损,记录时间当在后唐(923—936)以后。三,韦縠《才调集》卷一录“折钗破镜两无缘”“鸾飞远树游何处”二首,即《灯下闲谈》所录之前二首,但文本有很大不同,作者阙名,记录时间大约在前后蜀之间(936前后)。四,《太平广记》卷二七三引《本事诗》所录四首,坐实为刘禹锡遭李逢吉夺妓而作,参下节则所引文字全出《南楚新闻》,《太平广记》成书时间在宋太宗太平兴国间(976—984)。五,《刘宾客外集》卷七收《怀妓四首》,该集今存两种宋本,集则为北宋文献学家宋敏求编。据该集宋敏求跋,可以复原该集前八卷存诗的文本来源,且知此四诗全部录自《南楚新闻》。《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尉迟枢《南楚新闻》三卷”,载作者为“唐末人”,不言作者生平。《通志·艺文略》云“记宝历至天祐时事”,所记当源出今佚之《崇文总目》解题,是翻检原书后的记录。《太平广记》卷四九九引该书佚文有“是时唐季,朝政多邪”语,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认为“为五代人口吻,书当成于五代初”,我则认为更晚,因五代前期人还很少称唐末为“唐季”,至少应在后晋以后。也就是说,这一夺妓或夺妻故事,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流传,终于完全坐实为刘禹锡故事了。六,北宋时还另有传衍,一是《古今诗话》转录《本事诗》故事,二是刘斧《摭遗》引“青鸟去时云路断”句(《群英草堂诗余前集》卷下李景《浣溪沙》注引),皆晚出不必申述。
将以上记载分析一下,可以认为此组诗很可能原本为两组,即《本事诗》所录一首为一个单元,《灯下闲谈》所录三首为另一个单元,因诗风接近,到《南楚新闻》即捏合为一个故事。四首诗的作者,很可能如《才调集》所载,在唐末至五代前期即已不知作者。四首诗写得深情绵邈,伤怀欲绝,置于刘集自是俗调,民间读来确是难得的佳作,佳作就必須与名人联系,于是刘禹锡出现了。
至于刘禹锡与李逢吉之关系,我更愿意相信瞿蜕园先生《刘禹锡集笺证》附《刘禹锡交游录》之分析,李之登科较刘晚一年,到他元和十一年(816)为相以前,“与刘禹锡同游之日似不多,少有款曲,然亦当无怨隙”。元和后期,李与裴度、李德裕等为敌,刘禹锡于长庆、宝历间之政局,“身无所预”。到大和以后,“逢吉之势已衰”,刘与其来往,仅“虚与委蛇而已”。大和五年(831),李任东都留守,刘赴任苏州,李为其设宴款待,刘有诗《将赴苏州途出洛阳留守李相公累申宴饯宠行话旧形于篇章谨抒下情以申仰谢》,瞿认为“观诗题措语之谦谨,知其交情不深也”。对《怀妓四首》,瞿认为四诗“迥不似刘平日风格。‘怀妓’二字亦不合集中制题之例”,而刘损名下诸诗,“所改尤卑俗”。且分析,“禹锡若有家妓,其与白居易唱和诸诗中不应从未涉及,逢吉虽凶暴,亦恐不至举动如此无礼”,更认为附会者当因“知禹锡与逢吉素不相洽,假此以甚言逢吉之恶耳”。分析得体而可为结论。
最后,还是看一下《刘宾客外集》所录《怀妓四首》之原文吧:
玉钗重合两无缘,鱼在深潭鹤在天。得意紫鸾休舞镜,能言青鸟罢衔笺。金盆已覆难收水,玉轸长拖不续弦。若向蘼芜山下过,遥将红泪洒穷泉。
鸾飞远树栖何处,凤得新巢已去心。红壁尚留香漠漠,碧云初断信沉沉。情知点污投泥玉,犹自经营买笑金。从此山头似人石,丈夫形状泪痕深。
但曾行处遍寻看,虽是生离死一般。买笑树边花已老,画眉窗下月犹残。云藏巫峡音容断,路隔星桥过往难。莫怪诗成无泪滴,尽倾东海也须干。
三山不见海沉沉,岂有仙踪更可寻。青鸟去时云路断,姮娥归处月宫深。纱窗遥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料得夜来天上镜,只应偏照两人心。
诗中“玉钗重合”“蘼芜山下”“山头似人石”“画眉窗下”等语,皆古人言夫妻分合之常用语,与“怀妓”之题不合。今人高志忠《刘禹锡集编年校注》认为“是诗迥异刘诗,亦不类司空见惯、刺史断肠”,“无足可取,断非禹锡之诗”。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认为“词意浅薄,体格卑弱,亦不类禹锡诗”。所言皆是。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