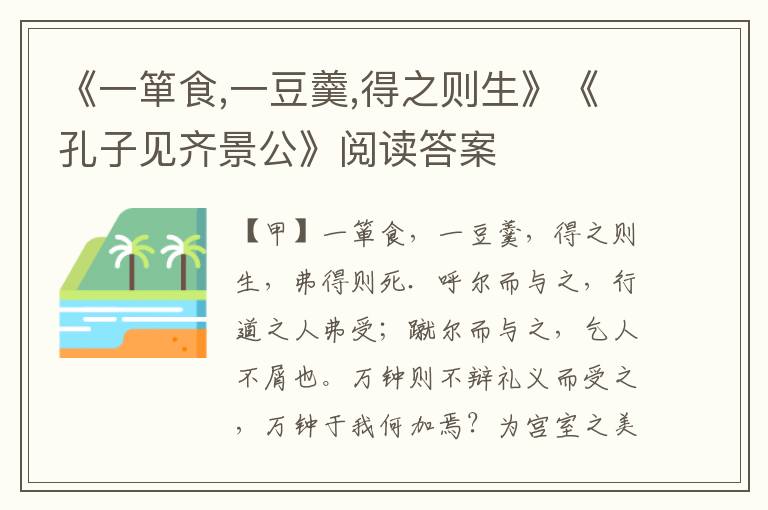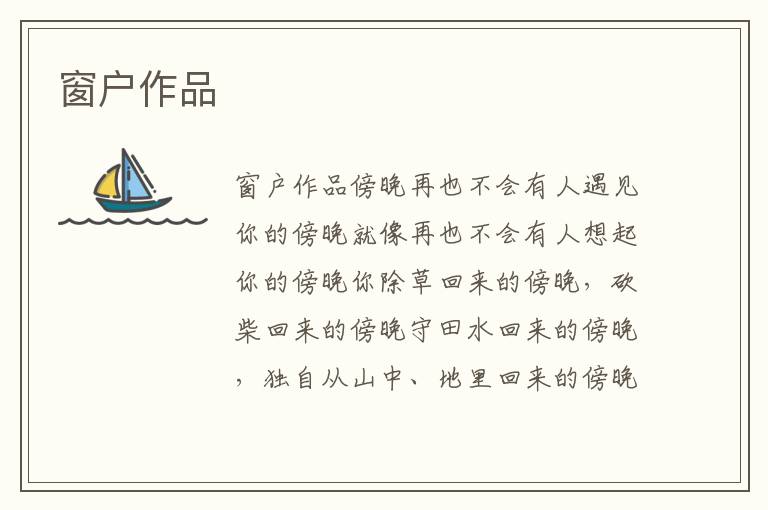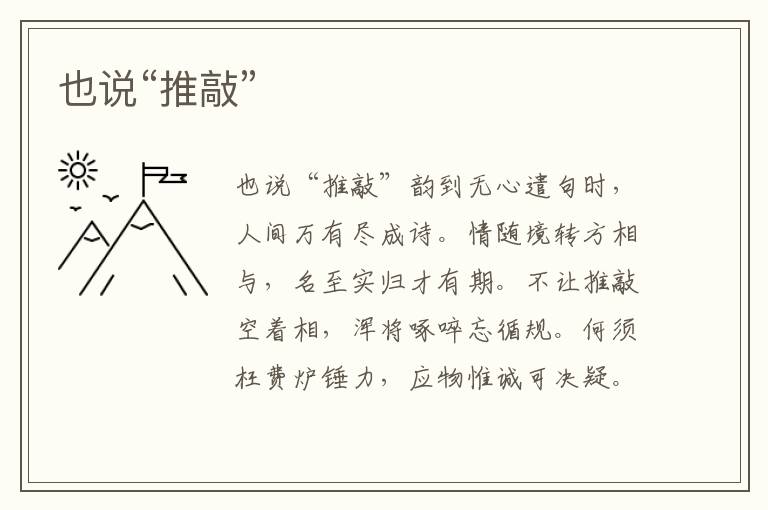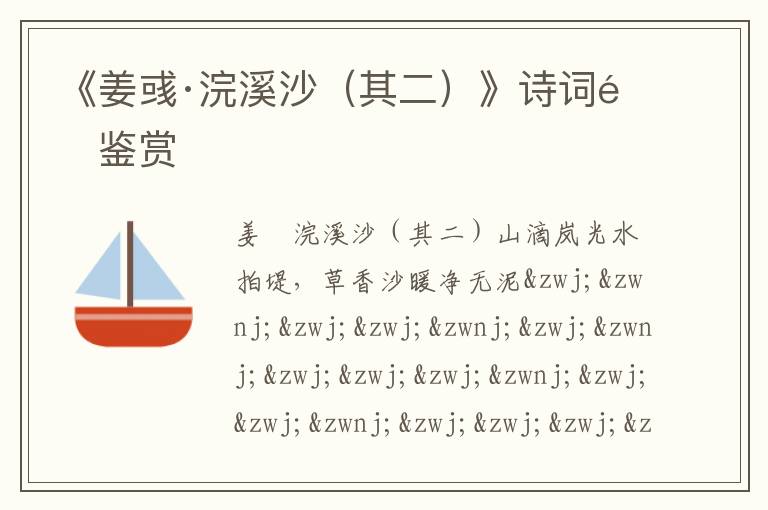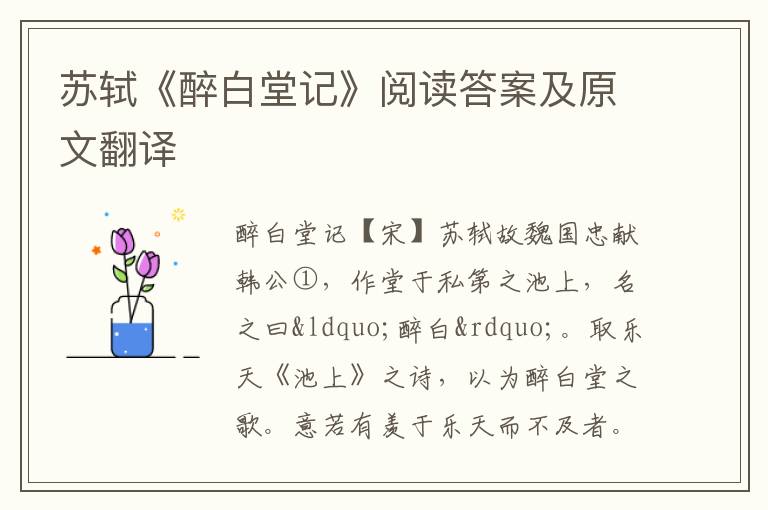【简介】感谢网友“雕龙文库”参与投稿,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方便大家学习。
三、 七国之乱之深远影响
七国之乱对于前汉政治之影响至为深广,它宣告高祖分封制之终结,汉随秦后,汉以反秦始,然而七国乱后,汉朝在职官制度上,基本上祖述秦朝的政治体制。《汉书·武五子传》记述燕剌王刘旦上疏曰:“高皇帝览踪迹,观得失,见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规土连城,布王子孙,是以支叶扶疏,异姓不得间也。今陛下承明继成,委任公卿,群臣连与成朋,非毀宗室,肤受之愬,日骋于廷,恶吏废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到武帝朝,削藩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然而武帝晚年也立即品尝了削藩导致的恶果,霍光之所以能够操弄大权,挟昭帝以令天下,此与汉刘宗室受到打压有绝大之关系,宗室被彻底边缘化,从而失去了对于朝政制衡的力量。因此,观刘旦上述言论,身为武帝之子,他亦有感于宗室之备受冷落,然而实质上,此根源于乃父、乃祖之酷政,刘旦岂可熟视无睹乎?唐李翰《汉祖吕后五等论》云:“揆夫高祖造汉,殷鉴亡秦,宗族无尺土之封,子弟立空虚之地,故众枝莫助而孤根易拔,封建之心肇于此矣。”(《文苑英华》卷七四一,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868页)世事得一利者或受一弊,尽获其利而丝毫不蒙其害者,实属罕见。高祖分封有当时形势之需要,而文景武帝削藩,也出自新时期新态势之诱惑,其历史必然性均不容否定。于是,前汉政治至此之走向,就须以平定七国之乱作为新的逻辑起点,此后前汉兴衰存亡都与之有不解之缘也!
《盐铁论·晁错》曰:“大夫曰:‘《春秋》之法,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故臣罪莫重于弑君,子罪莫重于弑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义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晁错变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室,侵削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亲,吴、楚积怨,斩错东市,以慰三军之士而谢诸侯。斯亦谁杀之乎?’”(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3页)武帝时期,朝廷诛灭淮南、衡山王之叛逆,实际上可以视为继七国之后,削藩行动之延续。若分析这段话,前半段关于淮南、衡山王,对照《汉书·武帝纪》元狩元年夏四月丁卯诏曰:“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这是武帝颁布的定谳之词,不容质疑。所以上述大夫前半段话,绝不敢为淮南、衡山申冤,要与武帝诏书保持一致,遂认同淮南、衡山咎由自取;而后半段话,却指斥晁错无事生非,以致宗室、诸侯、蕃臣和骨肉均与朝廷离心离德,削弱了汉刘政治之根基。言下之意,认为吴楚七国有蒙冤之哀痛,看到了汉刘政治已经陷入危机之中,颠覆了景帝消灭七国之正当性。
全祖望《题汉书吴王濞传后》云:“七国既败,乃下诏令诸将以多杀为功,想见天资之刻薄,追思杀三公以谢七国,不亦耻乎?予尝谓景帝最庸,唐昭宗尚不肯遽害杜让能,景帝出其下矣。既败而始令多杀,何不追雪三公耶?”(《鲒埼亭集汇校集注》,第1291页)景帝所作所为确实体现了其十分残忍的性格,然而,不可据此遽然认为景帝与文帝有显著的差别,《史记·孝景本纪》之“太史公曰”指出景帝如此行径,乃缘于“至孝景,不复忧异姓”,时势令景帝有条件肆无忌惮地削藩而已。景帝以及后继者疯狂地迫害吴楚叛乱者,《汉书·西域传》曰:“……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公主死,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妻岑陬。”楚王刘戊的孙女被当做和亲匈奴之“公主”,祸及子孙,其惨烈难言矣!
景帝乘势进逼,彻底瓦解藩国之威胁,即使在表面上尚需维持朝廷与宗室休戚与共的外在形式,而实际上诸侯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横遭剥夺。《汉书·高五王传》云:“自吴楚诛后,稍夺诸侯权,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设。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诸侯与朝廷已经形如陌路之人。
而且朝廷举措表里不一,十分虚伪,譬如《汉书·楚元王传》云:“汉已平吴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陆侯礼为楚王,奉元王后,是为文王。”按照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谈“景帝三年以后楚国沿革”云:“景帝三年,楚王戊反诛,其地本应尽入于汉,只因文景二代皆‘尊宠元王’,故立其少子礼为楚文王,以续楚元王后。因此刘礼之国仅有彭城及其附近数县之地。”(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楚元王之继位者实质上是徒有虚名罢了。
《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云:“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其相曰:‘王必欲应吴,臣愿为将。’王乃应之。相已将兵,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汉亦使曲城侯将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吴使者至庐江,庐江王不应,而往来使越;至衡山,衡山坚守无二心。孝景四年,吴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为贞信,乃劳苦之曰:‘南方卑湿。’徙王于济北以褒之。及薨,遂赐谥为贞王。庐江王以边越,数使使相交,徙为衡山王,王江北。”在七国乱中,淮南、衡山看似逃过一劫,但波澜不惊是暂时的,他们终究难躲厄运之降临,淮南王等对此了然于胸。周振鹤也谈及“济北国沿革(含平原郡)”云:“景帝三年,平定吴楚之乱以后,乘势收夺各诸侯国支郡,并且借更徙诸侯王之机,缩小其封邑。七国之乱,济北王未参与其事,不便削其版图,遂徙其王淄川,小其国。景帝四年,徙衡山王勃王济北,表面原因是酬其不反,但并不予其济北全部,而是乘机分济北置平原郡属汉,以缩小了的济北郡王之。同时,徙庐江王王衡山,收庐江、豫章二郡属汉。”(《西汉政区地理》,第105页)此种乾坤大挪移,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在处理藩国问题上,朝廷几乎可以高枕无忧了。
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编撰的《淮南子》,最典型地发泄了诸侯被削之愤懑,《淮南子·人间训》记载智伯招致祸害的缘由:“智伯求地于魏宣子,宣子弗欲与之。任登曰:‘智伯之强,威行于天下,求地而弗与,是为诸侯先受祸也。不若与之。’宣子曰:‘求地不已,为之奈何?’任登曰:‘与之使喜,必将复求地于诸侯,诸侯必植耳。与天下同心而图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于韩康子,韩康子不敢不予。诸侯皆恐。又求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于是智伯乃从韩、魏围襄子于晋阳。三国通谋,禽智伯而三分其国。此所谓夺人而反为人所夺者也。”(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3页)面对七王的悲惨下场,淮南王感同身受,其兔死狐悲之感,至为强烈。景帝至武帝,朝廷削藩势如破竹,所等待淮南王者,无非与七王一样,任其宰割,自己行将一无所有,此种焦虑,非他者所能体会。因此,淮南王视景、武二帝高举削藩之利剑,乃多行不义,一如智伯得寸进尺,欲壑难填。《淮南子·齐俗训》说:“智伯有三晋而欲不淡,林类、荣启期衣若县衰而意不慊。”上天不会永远眷顾得意者,武帝最后也会遇到克星,然后,受压迫者同仇敌忾,推翻景帝或武帝宝座,令他们亦如智伯一样,死有余辜,诸侯王得以一泄胸中积压之忿恨。此节文字,淮南王对“夺人而反为人所夺者也”,寄寓着不可告人之幻想。
而造化弄人,武帝身后,竟然由一年仅八岁的昭帝继位,据说其人实非武帝之子,果真如此的话,文帝之一脉在西汉的历史上也不过昙花一现耳!淮南王的诅咒竟然应验了!但是文景武祖孙三代至少以削藩改变了高祖所奠定的政治格局,前汉政治出现外戚擅权的新特征。
《汉书·楚元王传》云:“向每召见,数言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刘向所言,几乎成为前汉元、成、哀三朝政局的真实写照,岁月逾迈,直接导致了王莽之篡汉!
钱穆《国史大纲》也谈及西汉封建之兴衰,他说:“吴、楚七国乱后,宗室地位日削【宗室只宜封建,不宜辅政,以其地近而势逼。封建政制既不能复活,则宗室地位自难再兴。】,功臣传世渐久,亦不保其位【世臣与封建相扶翼,封建既不可复,世袭之制,亦不足持久。】,于是王室依仗乃惟有外戚【如景帝平吴、楚兼用周勃(功臣——应是周亚夫——笔者按)、窦婴(外戚)。武帝初立,窦婴、田蚡继相,皆外戚又渐得势之征】。”(《国史大纲》上册,《钱宾四先生全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80页)此种概括是精确的,其间,吴、楚七国之乱,堪谓前汉走向末路之重要原因,当一个政权出于人性之贪婪,毫不加以节制,并借助权势将此种人性的阴暗面极大化,甚至连有血缘的宗亲也要竭力排斥、摧毀,然则它与所有臣民的关系就更难以摆正,这个政权必定走向彻底的腐败,总之,不管它如何获取权力,其亡也忽焉,就成为历史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