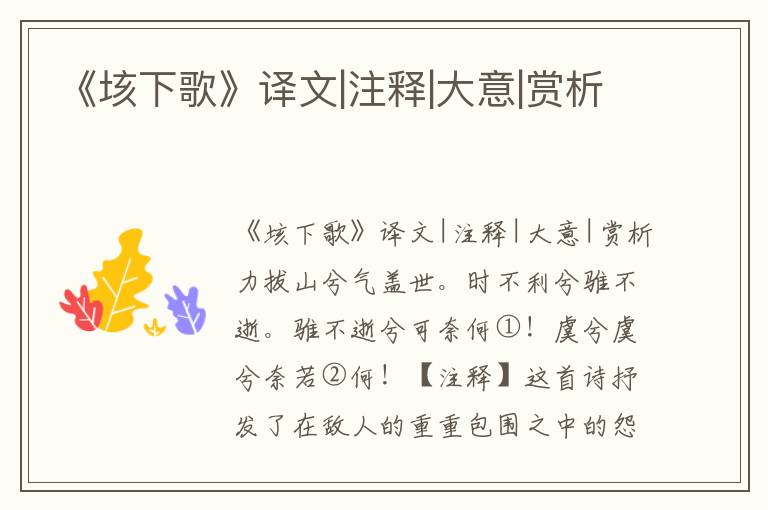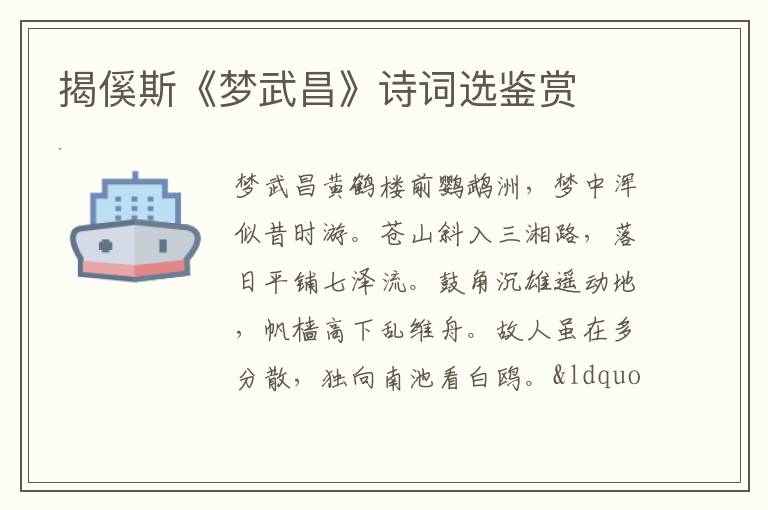【简介】感谢网友“雕龙文库”参与投稿,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方便大家学习。
欧阳玄
欧阳玄(1274—1358),字原功,号圭斋,祖籍江西庐陵,祖上迁居浏阳(今属湖南),延祐二年进士,天历初,初置奎章阁学士院,文宗亲署玄为艺文少监,纂修《经世大典》,又拜为翰林直学士,编修四朝实录,修辽、金、宋三史,为总裁官,累官至国子祭酒、翰林学士承旨,卒赠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曰文。著有《圭斋文集》15卷。明宋濂为其文集作序称:“公之文自擢第以来,多至一百余册,藏浏阳里第,尽毁于兵,此则在燕所录。自辛卯至丁酉,七年间所作。”则其著作流失大半。
欧阳玄在文学观念上与虞集、揭傒斯诸馆阁之臣较为接近,亦主“雅正浑厚”之风,一以唐、汉魏为宗。他在元中期之政坛、文坛皆地位显赫,“历官四十余年,三任成均,两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海内名山大川,释、老之宫,王公贵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辞以为荣。片言只字,流传人间,咸知宝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元史》卷一八二)。欧阳玄以在政坛、文坛之地位,对元中期,尤其是天历、至正年间“宗唐得古”之风气亦颇具推动之功。
欧阳玄论历代诗歌之变迁,亦以唐诗为盛,南宋以来衰弊已极,其云:
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为盛,逮及东都,其气寖衰,至李唐复盛,盛极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渐复于古,南渡以还,为士者以从焉无根之学而荒思于科试间,有稍自根拔者,亦多诞幻毕冗,不足以名家。其衰又益甚矣。(《潜溪后集序》,《圭斋文集》卷七)
欧阳玄所处的时代,正是诗坛“宗唐得古”之风如日中天的时期,亦是从郝经、戴表元、袁桷及虞集等人一致努力建立的新朝诗风已蔚成主流的时期,欧阳玄文中屡屡可见此种风尚,其云:“近时学者于诗无作则已,作则五言必归黄初,歌行乐府七言靳至盛唐。”(《萧同可诗序》,《圭斋文集》卷八)又云:“京师近年诗体,一变而趋古,奎章虞先生实为诸贤倡。”(《梅南诗序》,卷八)在《罗舜美诗序》中,更是自矜于这种盛世气象,“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于古”。且自赞元诗:“诗不轻儇,则日进于雅;不锲薄,则日造于正,诗雅且正,治世之音也,太平之符也。”可见,宗唐得古、归于雅正,几乎成为当时京华文坛一致的声音。
动辄言“雅正之音”、“治世之音”,学唐人学至此,流弊不免由此而生。学唐而徒有其浮廓的外表,堂皇的华服,而真正阔大的胸襟、高远的眼光并未具备,欧阳玄虽亦云“诗得于性情者为上”(《梅南诗序》,卷八),然而,在努力表现出一种“廉静”、“深醇”的涵养,追摹“冲和”、“雍容”的气度时,个体的性情、真挚的感情在诗中无疑已很难见到。欧阳玄言诗文宜“廉则不夸,静则不躁,深则不肤,醇则不靡”(《族兄南翁文集序》,卷八),以此种涵养的功夫,作有德君子、盛世文章,然而活泼泼的生命力自不免会从中流失。欧阳玄在论及江西文风时感慨道:“吾乡山水奇崛,士多负英气,然不免尚人之心,足为累焉耳。”(《族兄南翁文集序》,卷八)以奇崛、英气为累,亦见其所尚矣。
江西儒者文士集团
江西人文,在元中期仍颇负盛名。元三大儒之一的吴澄即活跃于江西,培养了许多学者文人,虞集即为其高足。文坛上江西籍的诗人亦颇为耀眼,除了在京的虞集、揭傒斯、范梈外,居于故乡,亦以文采风流、诗文名世者尚有刘辰翁之子刘将孙、庐陵刘诜等,他们对诗歌的领悟、对唐诗的解读不时有逸出主流之外的一些新见,给元代唐诗学增添了一份异彩。
一、折衷唐宋派:吴澄
吴澄(1249—1333),字幼清,号草庐,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奉诏求贤江南,被征入京,以母老辞归。至大元年(1308),召为国子监丞,升司业,谢归。英宗即位,拜翰林学士,同修国史。泰定初,为经筵讲官,后辞归,加授资善大夫。卒赠封临川郡公,谥文正。有《草庐集》诗4卷,清人合其所有著作为《吴文正公集》100卷。
吴澄为元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之一。揭傒斯《吴文正公撰神道碑》称:“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所以恢宏至道,润色鸿业,有以知斯文未丧,景运方兴。”可见吴澄、许衡为元代南、北学者之宗。《四库全书总目·吴文正集》又云:“衡之文,明白质朴,达意而止;澄则词华典雅,往往斐然可观,据其文章论之,澄其尤彬彬乎。”(卷一六六)
吴澄一生,虽几度仕元,但大半岁月仍僻居乡里,孜孜于学,“研经籍之微,玩天人之妙”,于江西学术与诗坛深具影响。就学术路径言,吴澄从学于程若庸,程受教于饶鲁,饶又为朱熹高足黄榦的学生,所以吴澄为朱熹四传弟子。江西又为陆学的大本营,因而,吴澄实乃折衷朱、陆学派而大成。就其诗学观念而言,一方面本于理学家的立场,另一方面则既有江西之传统,又与潮流相融合,因而,亦颇有折衷、调合唐宋的倾向。正因其哲学、诗学观念渊源复杂,然亦更见深度。其诗论主张,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唐诗为上品
吴澄并没有当时人立唐诗为一代典则的用心。对唐、宋诸大家亦皆深致倾心,绝不强分彼此、高下。然而就唐、宋两种诗歌范式而言,吴澄仍以唐诗为上品,这构成了吴澄唐诗观念的起点。其云:“颂雅风骚而降,古祖汉,近宗唐,长句如太白、子美,绝句如梦得、牧之,此诗之上品也。”(《胡助诗序》,《吴文正公集》卷一三)这正是元人“宗唐得古”的普遍主张。又在《萧独清诗序》中,以“清气”论诗,以此盛赞唐诗之美,其云:
诗也者,乾坤清气所成也。屈子《离骚》、《九歌》、《九章》、《远游》等作可追十五国风,何哉?盖其蝉蜕污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不滓,于楚俗为独清故也。陈拾遗《感寓》三十八,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超然为唐诗人第一。李翰林仙风道骨,神游八极,其诗清新俊逸,继拾遗而勃兴,未能或之先者,非以其清欤?朱子论作诗,亦欲净洗肠胃间荤血腥膻,而漱芳润。故曰诗也者,乾坤清气所成也。
从“清气成诗”这一角度,于历代诗歌独标《楚辞》与陈子昂、李白,以陈子昂为“唐诗人第一”,李白“继而勃兴”,后人难及,皆以其“清”。此“清”并非审美风格之“清丽”、“清峻”之类,“乾坤清气”者,更重在人格“清正”、“清高”,是“蝉蜕污浊”、“浮游尘埃之外”的高洁。有此襟怀,方有“湛湛如石井之泉,泠泠如松林之风”之诗品。吴澄喜以“清”论诗,如“形神两素淡,文行一清醇”(《送邓善之提举江浙儒学诗序》,《吴文正公集》卷一四)等。以“气”论诗,则反映出他作为理学家的立场。他以“气”运行来解释诗道之发生与变迁及诗体兴替,其云:
盈天地之间,一气耳。人得是气而有形,有形斯有声,有声斯有言。言之精者为文,文也者,本乎气也。人与天地之气通为一气,有升降,而文随之……宋不唐、唐不汉,汉不春秋、战国,春秋、战国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复少,天地之气固然。必有豪杰之士出于其间,养之异,学之到,足以变化其气,其文乃不与世而俱。(《别赵子昂序》,卷一四)
从“文本乎气”来说明诗道变迁之必然性,即承认“变”之必然性、合理性,从而亦承认宋、唐、汉、春秋、战国、唐虞各代诗文存在合理性,这对当时“复古”思潮实为一大反拨。
吴澄于唐诗人中最为称许陈子昂、李白、杜甫。其云:“李杜文章、才气、格力相抵,相视如左右手。”(《送邓善之提举江浙儒学诗序》,卷一四)李、杜并尊,为元代较普遍之风气,元人虽不满于宋人独尊杜诗,但元人亦甚重诗歌教化之用,因而,对杜诗仍有倚重,视为唐诗之极至。但从美学趣味上又更倾心于太白之“天才飘逸”、“潇洒不尘”,以其更具盛世之气象,吴澄亦具此意。《丁晖卿诗序》称:
李太白天才间气,神俊超然八极之表,而从容于法度之中,如夫子之从心所欲而不踰矩,故曰诗之圣。
历来以“诗仙”称李,“诗圣”称杜,吴澄则以“诗之圣”标举太白,言其“超然八极”而“从容法度”,称之至矣。以李白为法度之正宗,与宋人异,而正开明代风气。吴澄对陈子昂之赏拔,则重在其“始振风雅”。宋人重陈子昂者不多,宋末刘克庄《后村诗话》始有云:“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间,一扫六朝之纤弱。”而元人则关注有加。元人“宗唐得古”之倡,举复兴“风雅”为旗帜,正与陈子昂“始变雅正”(《新唐书》卷一○七《陈子昂传》)颇有相通。吴澄、范梈、欧阳玄、马端临、杨士弘、辛文房等皆对子昂甚为激赏。吴澄云:“伯玉甫唐家第一,卓然为李杜所师。”(《陈景和诗序》,卷一三)这也反映了元人较为关注唐诗中卓有古意、风骨高迈的一类,即以唐通于汉魏者,此正合于元人“宗唐得古”、“以晋参唐”之诗学主张。
(二)唐宋并尊
吴澄虽对唐诗深致称许,但并不菲薄宋诗,且常以唐宋并称,以李、杜、王、苏并举,俱称“唐宋高品”。他称道胡器之诗,“古体诗上逼晋魏,近体亦占唐宋高品”(《胡器之诗序》,卷九),与元人动辄抑宋,颇不相类。又云:“近世之为诗者……求其一句能如‘池塘春草’、‘枫落吴江’之可传者或鲜矣,况望其能如唐之陈、李、杜、韦,宋之王、苏、陈,可以成一家而名后世也哉!”(《张仲默诗序》,卷九)以唐之陈、李、杜、韦,与宋之王、苏、陈并举,正以其各显风流。在《刘巨川诗序》中亦以唐宋为诗家之模范,其云:“刘济巨川,才气健,格律正,琢句炼辞,虽唐宋大诗人,殆不是过……然则其可李、可杜、可王、可苏否乎?曰:可。”以李、杜、王、苏并为一代大家,唐宋并尊之意甚明。这是对当时诗坛过于“宗唐抑宋”之风的反拨。在《皮昭德诗序》中吴澄对贬宋之风还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云:
近年乃或清圆倜傥之为尚,而极诋涪翁。噫!群儿之愚尔,不会诗之变,而该夫不一之变,偏守一是而悉非其余,不合不公,何以异汉世专门之经师也哉。
指诋黄庭坚,正是宋末元初反对江西诗派时的激烈主张。吴澄对这些矫枉过正、执于门户的做法十分反感,以“群儿之愚尔”相斥。江西诗派固有其弊,宋诗固有其陋,但对宋一代大家,王、苏、黄、陈之流,吴澄倾力回护,不容时流任意轻贱。“偏守一是而悉非其余”,实为当时许多追逐时流者偏狭而极端的思维习惯,因而,对于能不为时风左右者,吴澄甚为赞许,他称道诗人聂咏夫,“分派江西,拾级半山,而睥睨唐人”(《聂咏夫诗序》,卷九),称道董震翁,“不选不唐,不派不江湖”(《董震翁诗序》,卷九),唯以简斋悟入,能出能入,终得神化之妙。皆是称扬独立于潮流之外,却能不失自我之精神者,对于诗坛愈来愈强盛的模唐拟唐之风,亦不失为一种颇有意义的反思。
吴澄的反思还表现在对唐诗,甚而是李、杜之作,亦保持一份理性与客观,在《邬迪诗序》中,其云:
太白《古风》压卷,子美《秦蜀纪行》如画。若“悲来乎”,若“笑矣乎”,非太白诗,伪作也;若“黄四娘家花满蹊”,若“南市津头有船卖”,虽子美诗,漫作也……迪之倜傥俊迈,吾惧其易流于此,故举李之《古风》、杜之《秦蜀纪行》……以勉。
太白诗中有“伪作”,杜甫诗中有“漫作”,不可学,则李、杜诗也需善加取舍。又如《唐诗三体家法序》论唐诗诗法云:
言诗本于唐,非固于唐也。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于唐而止也。于一家之中则有诗法,于一诗之中则有句法,于一句之中则有字法。谪仙号为雄拔,而法度最为森严,况余者乎?立心不专,用意不精,而欲造其妙者,未之有也。元和盖诗之极盛,其体制自此始散。僻事险韵以为富,率意放辞以为通,皆有其渐,一变则成五代之陋矣。异时厌弃纤碎,力追古制,然犹未免阴蹈元和之失,大篇长什未暇深论,而近体三诗法则先坏矣。
这里亦以李白为唐诗诗法之典则,正是举李白为唐诗正宗之意。吴澄虽以唐诗为诗法精妙者,但以元和诗为极盛而衰之起点,即以元和诗风为五代、宋诗之滥觞,开后世“僻事险韵以为富,率意放辞以为通”之风气,因而吴澄认为元人极诋宋诗琐碎刻削、求奇求险求工之弊,实应溯源于唐元和诗法,此论较当时人之认识确要更为深入。
吴澄论诗法也有继承宋人处,但能有超越,有法而不拘于法,有形而“不形于形”。如其云“字有眼,句有法”(《邬性传诗序》,卷九),又云“其言蔼然,其味悠然”(《邬性传诗序》,卷九),则是本乎江西,而参以情味、感兴;又在《何友闻诗序》中称:“诗贵有其影、有其神,而无其形。何友闻诗篇无滞句,句无俚字,机圆而响清,虽未遗于形,而已不形于形。”意为学诗虽需推究诗法,而终需超越形迹,以得其影、通其神为妙。机圆、响清之类,亦是宋人的话头,但吴澄能较为合理地借鉴,成为其诗学主张的一部分。这些亦是他较好地融合唐、宋诗学之处。
(三)唐宋诗之因革
吴澄与刘壎一样,欲探寻唐、宋诗之间更为深层的内在联系,而非简单地作此是彼非的褒贬。刘壎善用比较与辩证的眼光,寻找唐、宋诗中“异中之同”,吴澄则以“变化”的眼光来寻找唐、宋诗之间“因”与“革”的关系。一切诗歌发展变化皆有其继承性,即“因”,亦有其创新性,即“革”。其《皮昭德诗序》论道:
诗之变不一也……《诗》亡而楚骚作,骚亡而汉五言作,讫于魏晋。颜、谢以下,虽曰五言,而魏晋之体已变;变而极于陈隋,汉五言至是几亡。唐陈子昂变颜、谢以下,上复晋、魏、汉,而沈、宋之体别出。李、杜继之,因子昂而变;柳、韩因李、杜又变……诗之体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体,各以其才,各成一家,信如造化生物,洪纤曲直,青黄赤白,均为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概齐,而况后之作者乎?宋氏王、苏、黄三家,各得杜之一体。涪翁于苏迥不相同,苏门诸人其初略不之许,坡翁独深器重,以为绝伦,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己者如此。
此种变化的眼光于今人或不足为奇,然在当时,实不失为特出之见。他以“变”为中心,勾勒了从《诗三百》至宋代千余年诗体的演变过程,指出有不得不变之理,从而承认各种变化、各种存在的独特价值,“如造化生物,洪纤曲直,青黄赤白,均为大巧之一巧”。这种识见在当时颇为难得,元人崇古之风极盛,以唐溯汉魏,以汉魏复风雅的诗学思路,易使学诗者好古厌今,流于偏执,吴澄“均为大巧之一巧”的呼吁,事实上已肯定了“诗之变”为诗歌发展之必然,从而还宋诗以存在的合理空间。吴澄还探寻了唐诗与宋诗之因革关系,指出宋诗王、苏、黄三大家,“各得杜之一体”,以此来肯定宋诗本身即蕴含着对唐诗继承的因素,因而唐、宋诗之间并非不可兼美。在《诗府骊珠序》中,吴澄亦论及唐诗之因与革,其云:
呜呼!言诗,颂、雅、风、骚尚矣。汉、魏、晋五言讫于陶,其适也。颜、谢而下勿论,浸微浸灭,至唐陈子昂而中兴。李、韦、柳因而因,杜、韩因而革。律虽始于唐,然深远萧散不离于古为得,非但句工、语工、字工而可。
从诗歌之因与革的角度,吴澄把唐诗人李、韦、柳、杜、韩分为两类,李、韦、柳偏于继承,杜、韩偏于变革,吴澄皆肯定其价值。这种分类,事实上突出了唐诗与宋诗的深层关联,正是杜、韩诗中蕴含着唐诗转向宋诗的变机,因而,对杜、韩“诗之变”的评价,事实上即隐含着对宋诗肯定的态度。从这个意义而言,李白、杜甫虽同时,且都代表了唐诗最为卓越的成就,但事实上一个代表了一种典范的完成,另一个则标志着新的审美时尚的开端。根据是承前还是启后,是“因”还是“革”,将李、杜分而析之,在元代吴澄是独具只眼的一人。从这一角度,颇能把握唐、宋诗之分野,亦更能把握唐、宋诗内在的传承关系,从而在尊唐抑宋的思潮之下,吴澄为宋诗寻找到了更深层、更合理的评价尺度。
(四)超越唐宋:“品之高,其机在我”
吴澄既肯定“诗之变”为诗歌发展之必然,在“因”与“革”中,重视诗之“革”的作用,则在古与今、人与我中,更重视诗之今与诗之我。在《孙静可诗序》中,吴澄对此有充分阐述:
孙静可诗甚似唐人,或者犹欲其似汉魏。夫近体诗自唐始,学之而似唐,至矣。若古体诗,则建安、黄初之五言、《四愁》、《燕歌》之七言诚为高品,然制礼作乐因时所宜,文章亦然。品之高,其机在我,不在乎古之似也。杜子美,唐人也,非不知汉魏之为古,一变其体,自成一家,至今为诗人之宗,岂必似汉似魏哉?然则古诗似汉魏可也,必欲似汉魏则泥。此可为圆机之士道,执一废百者未足与议也。
近体学唐,古体学汉魏,正为当时风气,但吴澄并没有汇聚到陶醉与赞美此种时风的潮流中去,他提出“品之高,其机在我,不在乎古之似也”。自严羽《沧浪诗话》提出“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元人亦倡导“近体主于唐,古体主于《选》”,以浑厚、高古、醇雅为尚的风气笼盖整个诗坛。难免不千人一面,千诗一腔,亦步亦趋。元初赵文提出“诗多人少”,即是呼吁“诗中之人”,吴澄“其机在我”,亦是呼吁“诗中之我”,“我”之精神、灵魂、性情、意志。“杜子美,唐人也,非不知汉魏之为古,一变其体,自成一家,至今为诗人之宗”,杜诗能变,方为天下之宗,今人又何必泥于尊古而不变!因而,吴澄提出“古诗似汉魏可也,必欲似汉魏则泥”,对于一味崇古宗唐之风实有救弊之用。在《朱元善诗序》中,吴澄进一步发挥此意,且论及学诗三境界,其云:
不能诗者联篇累牍,成句成章,而无一字是诗人语。然则诗虽小技,亦难矣哉。金谿朱元善才思俱清,遣辞若不经意,而字字有似乎诗人,虽然,吾犹不欲其似也,何也?诗不似诗,非诗也;诗而似诗,诗也,而非我也。诗而诗已难,诗而我尤难。奚其难,盖不可以强至也。学诗如学仙,时至气自化。
“诗不似诗”,无一字是诗人语,自不足道;学到“诗而似诗”,则技法娴熟、字字似有诗人,但自我之精神仍无;惟到“诗而我”的境界,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诗人。“诗而诗”的境界需“学”,“诗而我”的境界则需“化”,“变化”、“融化”、“陶化”,使我与诗,我与人,我与物交融相契,方自然成诗。因而,吴澄反对“似”,强调“真”,“虽形似超超于青冥风露之上,而人也方与蜣琅蝇蚋同梦而未醒”(《黄成性诗序》,卷一○),如何能得高风清标之诗?在《何敏则诗序》中,吴澄对模拟形似之风更作了批驳,其云:
天时物态,世事人情,千变万化,无一或同,感触成诗,所谓自然之籁,无其时,无其态,无其事,无其情,而想像模拟,安排造作,虽似犹非,况未必似乎?
天时物态、世事人情,千变万化,而学诗之人徒具声色酷似,模拟形似,如何能得真诗真境、真性真情?从这一角度而言,吴澄主张学诗作诗终需超越门户、超越唐宋,甚或超越古今,一本性情之真。其赞谭晋明诗,“天才飘逸,绰有晋人风致,其为诗也,无所造作,无所模拟,一皆本乎情之真。潇洒不尘,略无拘挛、局束之态……非学陶、韦,而可入陶、韦家数者也”(《谭晋明诗序》,卷一○)。然吴澄之“性情之真”,与元初赵文“人人有情性,则人人有诗”之性情,与元末杨维桢诸人“抗尘走俗,不谐于世”之性情皆不相类。吴澄所言之性情,乃经过理学涵濡后,天理人性相谐相容之情性,因而,此性情“光莹透彻,渣滓尽而冲漠存”(《黄成性诗序》,卷一六),乃“在人之心”与“在天之性”之和谐。因而,吴澄论诗虽不乏超越之精神,主张会通唐人、晋人之精神与风度,表现自我之情性,然而当诗人过于潜沉在“心与景融、物我俱泯”的境界中(《一笑集》,卷一○),吟咏、思考着天地与生命时,诗中之“我”,终究流失了许多活泼、新鲜的生命感受,未免远离了千姿百态、哀乐铭心的现实人生。
二、宗唐性灵派:刘将孙、刘诜
刘将孙(1257—?),字尚友,庐陵(今属江西)人,曾为延平教官、临汀书院山长。仁宗前期仍在世。其父刘辰翁以文名于宋末,当文体冗滥之余,欲矫以清新幽隽,所作蹊径独开,遂别自成家。将孙濡染家学,颇习父风,当日有“小须”之称。吴澄为其集作序,称其“浩翰演迤”,自成为“尚友之文”,曾以立序其集则谓“渊源所自,淹贯千古”,可见颇得时名。《四库全书总目·养吾斋集》评其诗曰:“今观其《感遇》诸作,效陈子昂、张九龄,虽音节不同,而寄托深远,时有名理。”(卷一六六)则其诗亦具唐风。有《养吾斋集》40卷,久佚,清人编《四库全书》时,自《永乐大典》等书中辑成32卷。
刘将孙的唐诗观念、诗学思想受同乡赵文影响颇深,将孙有《赵青山先生墓表》,极推赵文之文学,其云:“吾庐陵巽斋欧阳先生,沈潜贯穿,文必宿于理,而理无不粲然而为文。繇是吾先君子须溪先生与青山赵公相继。”谓庐陵自欧阳守道(巽斋)先生之后,惟须溪与青山相继相并。将孙则继承此二人之学,论学论文强调文道合一、文以气盛,乃秉承家学;论诗重性情笔力,则为青山衣钵。
赵文为宗唐性灵派的第一人,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性灵说之基本理论,在青山诗论中,已可说是大体完成了。”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页121。刘将孙、刘诜等人皆传承其说,使元代“宗唐得古”的诗学大潮中一股清新而灵性的支流得以流衍、延伸。刘将孙的唐诗学思想,概言之,有如下几方面:
(一)重“情”
元人学习唐人,有重在建立一代典则,从诗法、诗风、诗之格调等艺术规范上取法唐人者;亦有从唐人重性情、重感兴、重自然的艺术精神上取法唐人,且力图最终脱落涯岸、超越于前人者,宗唐性灵派即是后者。赵文如此,刘将孙亦然。
刘将孙重“情性”,此“性情”乃天然至真至纯之物,未为后天观念所修正者,因而不同于王义山、吴澄等理学家,亦不同于戴表元、赵孟頫等文臣之“性情”。其云:“文章犹小技,何况诗云云。沛然本情性,以是列之经。”(《感遇》五首之五)文章、诗歌本不足道,皆因其中“沛然本情性”,方足为万世之经典。在《本此诗序》中刘将孙论及其性情观:“诗本出于情性,哀乐俯仰,各尽其兴,后之为诗者,锻炼夺其天成,删改失其初意,欣悲远而变化非矣。人间好语,无非悠然自得于幽闲之表。”性情皆本天然,哀乐随心,俯仰尽兴,无需外饰与约制,悠然于心,自成人间好语。这里排除了“理”与“道”、“雅”与“正”等对情性的约束与限制,一本天然。既重情性之天然,则对唐诗之深于情者、情之至者,必深致倾心,在《魏槐庭诗序》中,他论道:
呜呼,诗固仁人志士、忠臣孝子之所为作也,岂直章句之巧而风月之尚哉!古所谓惊风雨、泣鬼神,非以其奇崛、突兀,以其志也。刺心血以食无母之凤雏者,杜陵之所以一饭不忘者也;呼穹穹与厚厚者,李习之所以识苦语之动神理者也;“天若有情天亦老”者,长吉之所以使金铜堕泪而能言者也;“此身无处哭田横”,玉川子之怨魄所以痛绝于玉泉之会者也;“白草建康宫,反袂哭途穷”者,徐骑省之所以辟言易世而无忍疵者也。二千年间,此语有数。
此与张潮《幽梦影》所云“古今至文,皆血泪所成”意有相近。这里所举之诗人杜甫、李翱、李贺、卢仝、徐铉,除杜甫外,余者皆难合正统派所倡言之性情和正、哀乐中节者,然皆感发真挚,深含至情,其感天动地者正在于此。因而,刘将孙之重性情,实含有偏重于“情”的倾向,此为性灵化的表征之一。明清两代性灵派标举“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张潮《幽梦影》),“人者,情种也,人而无情,不至于人矣”(张琦《衡曲麈谭》)之类,实开自元人。
唐诗之抒情有两种,一类合于温柔敦厚、中和之美,得其情性之醇正,乃“致君尧舜上”、“感时花溅泪”者,足见其诚挚、恳恻之意;一类难合于中正之道,惟一往而情深,或飞扬跋扈,哀感顽艳,偏于奇情率性,深含至情至性者。元人正统观念中,多推尊前者,而刘将孙显然于后者更多关注。从此角度出发,他最为推崇唐诗人李贺,在《刻长吉诗序》中其云:“先君子须溪先生于评诸家诗最先长吉……每见举长吉诗教学者,谓其思深情浓,故语适称,而非刻画无情无思之辞,徒苦心出之者。若得其趣,动天地、泣鬼神者固如此。”又云“最可以发越动悟者,在长吉诗”,可见推崇之隆。宋元之际,李长吉诗颇风行,然人们多赏其奇诡、幽异之辞章,如北人赵衍所云:“逮李长吉一出,会古今奇语而臣妾之。”(《重刊李长吉诗集序》)刘将孙则以“思深情浓”一语,以情之至者为誉,使解读李贺诗获得一新的角度,同时也表明元人对唐诗抒情功能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这表明,唐诗中“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深知身在情常在”(李商隐《暮秋独游曲江》)之类的情语、痴语,虽不尽合于中正之音、中和之美、雅正之道,然呈现出的却是隽永深情的性灵世界。在突破“礼”与“理”的约束之后,再度深入到人们的视域与心灵之中。
以“情”为归趣,自然对于当时各种缺少“情味”的拟袭之作,皆致不满。其云:
余尝怃然于世之论诗者也。标江西竞宗支,尊晚唐过风雅。高者诡选体如删前,缀袭熟字,枝蔓类景,轧屈短调,动如夜半传衣,步三尺不可过。至韩苏名家,放为大言以概之,曰:“是文人之诗也。”于是常料格外,不敢别写物色;轻愁浅笑,不复可道性情。(《黄公诲诗序》,《养吾斋集》卷一一)
元初,江西、四灵、江湖诸派,衰而未绝,同时,宗唐得古之风日盛,或主盛唐、或张选体,各以门户自高,“步三尺不可过”,诗中遂不复有真性情。刘将孙大力呼吁“诗者,所以自乐吾之性情也”(《九皋诗集序》,卷一○),“诗不为某家某体……各随性所近,情景尽兴,已极刷洗,楚楚如清风之泛春服”(《黄公诲诗序》,卷一一)。然如何“自乐吾之性情”呢,刘将孙特主“清气”之说。
(二)主“清气”
以“清气”论诗,不始于刘将孙,实为中国传统诗论的重要命题之一。“气”分清浊、轻重、精烦等,《黄帝内经·阴阳应象》云:“清阳为天,浊阴为地。”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则引入清、浊之气以论文。《世说新语》大量用“清”来品鉴人物,《文心雕龙》、《诗品》大量以“清”来品藻诗文,清刚、清典、清奇、清越、清拔等概念遂构成了极其丰富的“清”美艺术世界。
元人的审美理想中也有对“清”的不懈追求。如赵孟頫、吴澄等人的诗论皆有关于“清”之阐释,然元人最注重以“清气”论诗者,首推刘将孙。在《彭宏济诗序》一文中,他对“清气”有颇充分的阐释:
天地间清气,为六月风,为腊前雪,于植物为梅,于人为仙,于千载为文章,于文章为诗。冰霜非不高洁,然刻厉不足玩,花柳岂不明媚,而终近妇儿。兹清气者,若不必有,而必不可无。
在这里,刘将孙赋予“清气”以极高的地位。何者为清气?言莫能尽意,立风、雪、梅、仙诸象以尽之。在《九皋诗集序》中又以鹤为喻,对此有更充分的阐释,其云:
嗟乎!天地间何往而非声也。天簌莫如风,而翏翏,而调调可尔;而呼,而号,而激,而叱,披靡之不给,而听者有厌之者矣。莺之绵蛮也,燕之呢喃也,宁不可爱,而过之也,有忘之者矣。若夫感赏于风露之味,畅适于无人之野,其鸣也非以为人媚,其闻也非其意,而得之缥缈者,无不回首萧然;虽肉食之鄙夫,筝笛之聋耳,将亦意消而神愧,则惟九皋之鹤声为然。故曰声闻于天,非天不足以知之。凡声者不过闻于人而已,孰能闻于天?九皋何许,天高听下复何以加焉?物之负清气,出乎其类者如此。
这里举了三种声音:风声、莺啼、鹤鸣,天簌莫如风,然犹有听而厌之者;莺燕之呢喃,犹有过而忽之者;唯“声闻于天”之九皋鹤声,令人“意消神愧”。物之负清气者如此,诗人作诗,必得此方能性情自得、清气流贯:
人声之精者为言,言之精者为诗,使其翩翩也皆如鹤,其诗之矫矫也,如其鸣于九皋,将人欲闻而不可得闻,诗至是,始可言趣耳。夫诗者,所以自乐吾之性情也,而岂观美自鬻之技哉!(《九皋诗集序》,卷一○)
诗人若能如鹤之鸣,其人必“飘飘乎如青田之君子”,“泠泠乎如花表之仙人”(《九皋诗集序》,卷一○),其作必“因物所感,高山流水;适契琴趣,混合自然。眼前意中,宛然不食烟火,谈笑有风骨”(《彭宏济诗序》,卷一一)。这里,刘将孙赋予了秉“清气”之诗人以最高之美质。因而,刘将孙所谓“清气”与一般审美风格上之“清”颇有不同,审美风格之“清”常对应着一种具体的审美风范与品质,而刘将孙之“清气”更具整体意义与形上色彩,它涵盖并超越于各种诗歌风格、形式,是更本质的存在。在他看来,有“清意”然后有真诗,其云:
自风雅来三千年于此,无日无诗,无世无诗,或得之简远,或得之低黯,或得之古雅,或得之怪奇,或得之优柔,或得之轻盈,往往无清意,则不足以名世。(《彭宏济诗序》,卷一一)
无论何种诗风,皆必具“清意”,此为诗歌名世的必要条件,可见清气乃指诗歌的本质精神。在《九皋诗集序》中刘将孙进一步论及秉清气之诗人所应有之特质:
欣悲感发,得之油然者有浅深,而写之适然者有浓淡,志尚高则必不可凡,世味薄则必不可俗,故渊明之冲寂,苏州之简素,昌黎之奇畅,欧之清远,苏黄之神变,彼其养于气者落落相望,皆如嵇延祖之轩轩于鸡群,宜其超然尘埃混浊之外,非复喧啾之所可匹侪。
刘将孙所举历代诗人中最具清气之质者,陶、韦。然韩、欧、苏、黄,诗风迥然,亦皆具超然尘埃之表之清气。以韩、欧、苏、黄为具“清气”者实为刘将孙独具之眼光。“清”自有绝俗、清高之意,所谓“世味薄则必不可俗”,所谓“超然尘埃”、“意空尘俗”(《胡以实诗词序》,卷一一),“飘飘君子”、“萧然书生”(《九皋诗集序》,卷一○)即此。这一类诗人中,刘将孙首推韦应物,以韦诗“悠然者如秋,泊然者如水”(《清权斋集序》,卷一○)。但在刘将孙看来,这之中未免又少了一种浩荡、劲拔之气,因而,刘将孙又赋予“清气”以新义,即“劲拔、清刚、浩荡”之气,以韩、欧、苏、黄相济,所谓“浩荡奇伟”、“古雅磅礴”(《谭村西诗文序》,卷一○)、“摩厉飞动”、“神迈千古”(《黄公诲诗序》,卷一一)即是。这一类诗人中,刘将孙最倾心韩愈,屡称“昌黎奇畅”、“韩柳大家”(《赵青山先生墓表》,卷二九),认为“昌黎之古文,其小律小绝,无不精妙”(《谭村西诗文序》,卷一○),“三千年间,惟韩、欧、苏独行而无并”(《须溪先生集序》,卷一一)。因而,刘将孙之清气,即有清空无尘之味、亦有浩荡汪洋之势,惟如此,才得“宛然不食烟火,谈笑有风骨”之绝俗与酣畅,得“清”而姿态万千,“大之而金石制作,歌《明堂》而诵《清庙》;小之而才清婉娈,清《白雪》而艳《阳春》,古之而鼎彝幼渺,陈淳风而追泰古;时之而花柳明媚,过前川而学少年”(《九皋诗集序》,卷一○)。因而,其“清气”流转于古今、大小,不拘于浓淡、深浅,既是一种超凡绝俗的生命态度,亦是一种刚劲峻拔的生命力度,惟如此,则清而不枯、清而不淡、清而不弱,清而寥廓,清且浩瀚。在他看来,唐诗之清,正是如此,“此盛时作者,如浑河厚岳,不假风月为状;如偃松曲栢,不与花卉争妍,风气开而文采盛”(《天下同文集序》,卷九)。这正是刘将孙于唐诗人中特取韩愈与韦应物相济相合之用心。
“清以气,气岂可揠而学、揽而蓄哉!”(《彭宏济诗序》,卷一一)“气”不可学,惟得于性情。“人间好语,无非悠然自得于幽闲之表”(《本此诗序》,卷九),即诗惟“发之真”、“遇之神”、“悠然于心”,以自然之趣、自得之境、表自我之真,方能不泯、不朽,方有清气流贯,长存世间。此与明清性灵诗说正如出一辙。
刘诜(1268—1350),字桂翁,号桂隐,庐陵(今属江西)人。少颖悟,蔚然有老成气象,宋之遗老巨公以振起斯文期之。曾肆力于名物、度数、训诂、笺注之学,十年不第,乃刻意于诗、古文,以师道自居,声誉日隆。江南行御史台屡以教官馆职、遗逸荐,皆不就。卒谥文敏。有《桂隐文集》4卷、《桂隐诗集》4卷。
刘诜虽为一介布衣,然其诗文亦为一时之盛,对当时诗坛文坛风气有较大之影响。又因僻居乡野,且历经延祐之治与元末之乱,其诗学思想、美学趣味、唐诗观念与馆阁文臣们相比,自有其独到之处。
其诗学思想主要在“宗唐”与“自立”。元中期“宗唐复古”之风演为极盛,因而诗坛亦滋生出一股拟袭之风、门户之习,刘诜有感于此,特主自抒胸臆。《元史·儒学传》称其“根柢六经,躏跞诸子百家,融液今古,而不露其踔厉风发之状”(卷一九○)。可见其学有根柢,然能融液于己。欧阳玄在《桂隐文集序》中称道曰:“至论其妙,非相师,非不相师。”《四库全书总目·桂隐集》亦云:“盖其文章宗旨,主于自出机轴,而不以摹拟字句为古。”(卷一六六)“非相师,非不相师”,指其学而能化。刘诜对唐诗之态度,正如此。
在《与揭硕曼学士书》中,刘诜云:
古今文章,甚不一矣。后之作者,期于古而不期于袭,期于善而不期于同,期于理之达、神之超、变化起伏之妙,而不尽期于为收敛平缓之势。一二十年来,天下之诗,于律多法杜工部《早朝大明宫》、《夔府》、《秋兴》之作,于长篇又多法李翰林长短句。李杜非不佳矣,学者固当以是为正途,然学而至于袭,袭而至于举世若同一声,岂不反似可厌哉?……故学西施者,仅得其顰,学孙叔敖者,仅得其衣冠谈笑;非善学者也。故李、杜、王、韦,并世竞美,各有途辙,孟荀氏、韩柳氏、欧苏氏,千载相师,卒各立门户。
这段话既表明刘诜对唐诗之态度,亦见其诗学主张之核心。“李杜非不佳矣,学者固当以是为正途”,“李、杜、王、韦,并世竞美”,“宗唐”意味亦浓,这是其论诗重“学”的一面。另一方面,学诗更需“善学”,即“期于古而不期于袭,期于善而不期于同”,刘诜并不反对学古,但反对袭古,学古宜得其古意,而非袭其古貌,因而今人“宗唐”与“得古”,皆需“学”而非“袭”,“学”则通于古人之理、神、妙,然后各立门户。这也是李杜王韦并世为美,又各有风标的法门所在。“袭”则徒得唐人衣冠、皮相,因而刘诜论诗,以“宗唐得古”为基础,但同时更重视“变化为妙”、“以自为古”(《与揭硕曼学士书》)。陶铸百家,又自出机轴,终不失自我之真。在这一点上,他与赵文、刘将孙诸人可称同调。在愈来愈浓郁的宗唐复古、学唐师古的潮流中,一直有一股以自我之性灵为重的潜流,它代表了宗唐的另一种门径。这种方式在元末因世乱俗离而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强烈,并由此产生了元代最有价值的诗篇、最具创造性的诗人。
刘诜以清士自居,其美学趣味与身居朝廷、倡为雅正、高鸣太平的主流趣味不尽相同,因而对唐诗艺术意境之认同与接受亦有不同。他溯古体、歌行之流变:“诗之为体,三百篇之后,自李陵、苏武送别河梁,至无名氏十九首,曹魏六朝,唐韦柳为一家,称为古体。自汉《柏梁》、《秋风词》,驯至唐李杜为一家,称为歌行。古体非笔力遒劲高峭不能,歌行非才情浩荡雄杰不能。”(《夏道存诗序》,《桂隐文集》卷二)以李杜、韦柳分别为歌行、古体之大家,且上接汉魏,以此为诗之正途,以唐法古的倾向亦颇明显。取法李、杜,得诗之正,取法韦、柳,则体现了刘诜作为“清士”的审美趣尚,其云:
琢清贮澹,凝幽拔奇……飘乎如轻雪之度风也,冷乎如寒泉之落涧也,澹乎如古罍洗之不可杂众器也。(《夏道存诗序》,《桂隐文集》卷二)
飘忽、幽冷、古澹,代表着元代另一类审美趣味,属于对唐诗的另一种解读方式。他们优游山林,自居清标,因而,多幽深清寂之情、尚古澹离尘之美。其所赏之诗美,乃“如幽林晓花,真寂不赏;如寒机夜织,神专而心苦;如深山遗老,语言近质,终有德人深致”(《彭翔云诗序》,卷二),其境乃“真寂”、而非“枯寂”;若“苦”而不失幽静;遗老深山,而有悠然之远兴。这种隐,与乱世之隐,残山剩水之寄,终有不同。虽清寂而蕴生机,因而,不同于江湖、四灵之法晚唐,而专以韦、柳为法,兼采李、杜之大。其诗虽“独悲孤笑,危睇遐思”、“长吟思慕,高歌忧患”(《刘梅南诗序》,卷二),似乎逸出了延祐诗坛、京华文臣所高倡的盛世之雅音,雍容之气度,但仍有其格局,无衰疲之气。
本于这种尚古澹、野逸之美的倾向,刘诜诗论亦表现出重天机、自然的意味。以性灵与学力相济,天机与锻炼相参,《刘梅南诗序》云:“其靓丽者,如野桥夜月,学按霓裳,闻者莫不辨。其萧散者,如空山绝涧,时见幽花,行者回首……此岂独天机学问所到,亦用工然耳。”又云:“锻炼精确,而不废真意。”(《彭翔云诗序》,卷二)可见所尚乃虚、实相生,标缥缈、恍惚、灵动之境,而又有迹可寻。由此可知,刘诜之性灵意味较赵文、刘将孙诸人要疏淡,但其融液古今,独出性灵之主张,与赵文之脱落涯岸、刘将孙之“发之真、遇之神、悠然于心”的精神本质则又十分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