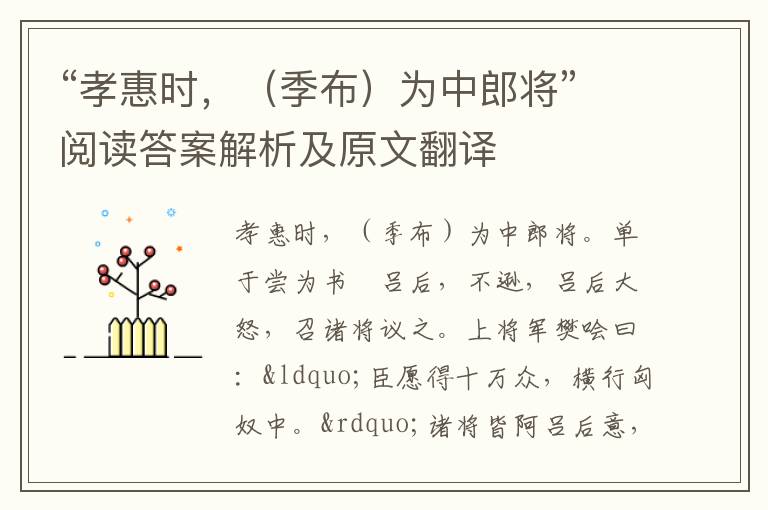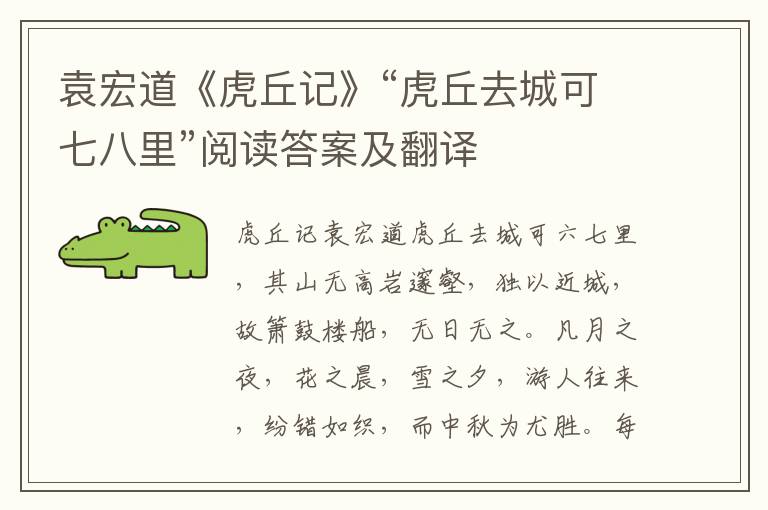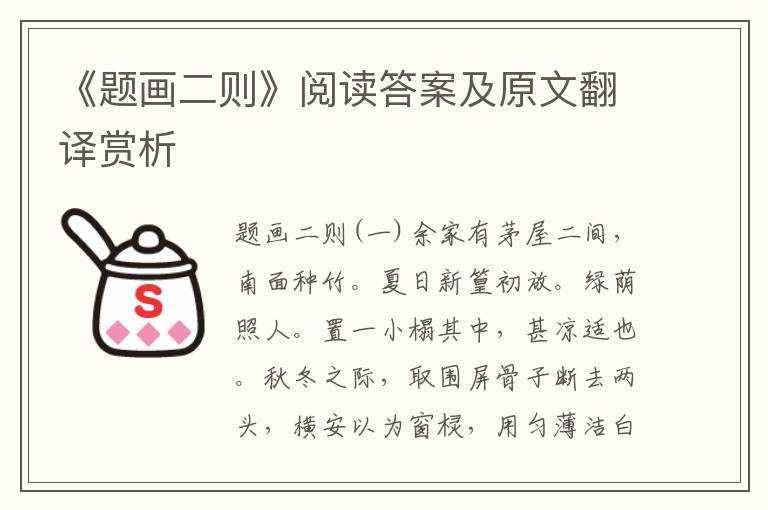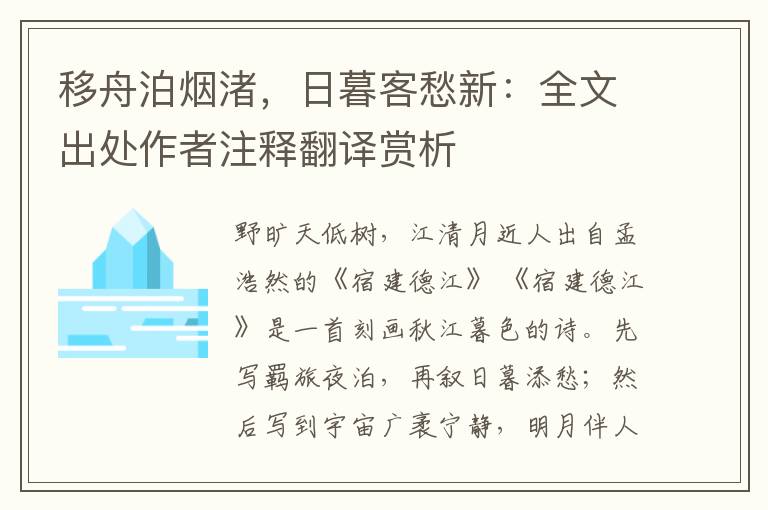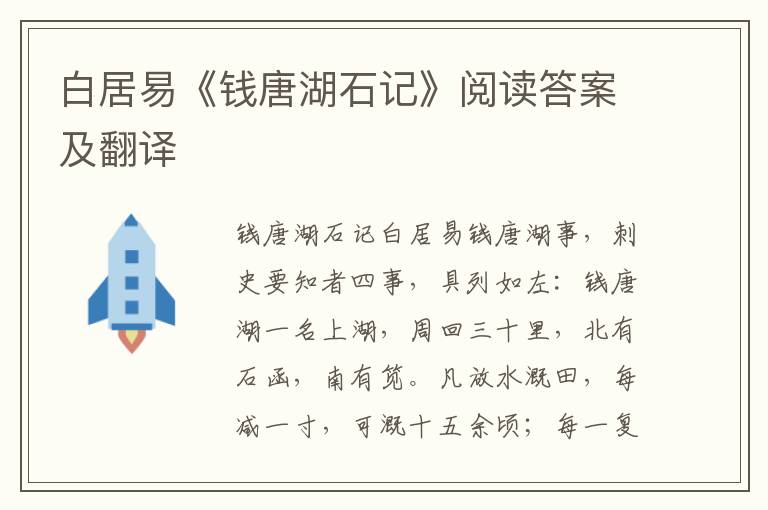【简介】感谢网友“雕龙文库”参与投稿,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方便大家学习。
幽默是人类天性,中国古人亦不例外。作为南方政权,六朝辖区主要在长江流域,相对于黄河所经北方地区,其自然环境则要优越得多,而物质条件优渥与文化繁盛密切相关。六朝烟水,鱼米之乡,人民谋生较易,精神亦享有余裕,生长于富庶温柔之乡的江南,经学式微,思想宽松,士人左琴右书,腹笥充盈,文学造诣较深,故此,文人戏谑,似乎压过了武士械斗,以文为戏,亦成时尚。南人和北人杂处共居,文化碰撞,更激发士人的幽默感,各种笑料乃士人之谈助。于是,在文人雅士生涯中,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它们是生活的调剂品。观刘义庆所编辑的《世说新语》之《排调》《轻诋》等,时人之好调笑,幽默细胞之发达,于此可见一斑。翻检关乎六朝的文献,里边记载文人间相互调侃的片段,令人不禁莞尔,笔者随手记下,以博同好者之一粲耳。
一、 六朝文人凭藉文字修养以表达讥刺刘勰《文心雕龙·谐》篇云:“‘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诙谐,就是用语辞来开玩笑,因而,历史上具有幽默感者,“诋嫚媟弄”,兴会万端,逗乐众人;《文心雕龙·谐》篇又云:“‘’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盖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与夫谐辞,可相表里者也。”隐语与后世借助语辞来制造谜语,以供竞猜谜底,颇有相似之处。刘勰将“谐”与“”勾连起来,人与人开玩笑是寻常事,然而,以文字游戏的形式,来开一个高智商或高文化的玩笑,亦谈何容易,因此,六朝文士似乎就独擅胜场了。
《南史·文学列传·卞彬传》记述:“彬险拔有才,而与物多忤。齐高帝辅政,袁粲、刘彦节、王蕴等皆不同,而沈攸之又称兵反。粲、蕴虽败,攸之尚存。彬意犹以高帝事无所成,乃谓帝曰:‘比闻谣云:“可怜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暂鸣死灭族。”公颇闻不?’时蕴居父忧,与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谓沈攸之得志,褚彦回当败,故言哭也。列管谓箫也。高帝不悦,及彬退,曰:‘彬自作此。’后常于东府谒高帝,高帝时为齐王。彬曰:‘殿下即东宫为府,则以青溪为鸿沟,鸿沟以东为齐,以西为宋。’仍咏诗云:‘谁谓宋远,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摈废数年,不得仕进。乃拟赵壹《穷鸟》为《枯鱼赋》以喻意。”在宋齐易代之际,褚渊,字彦回,他是宋朝的贰臣,《南齐书》本传记其“轻薄子颇以名节讥之”,而袁粲、王蕴和沈攸之等皆反对萧道成篡宋,堪称宋朝死节之臣,当袁粲和王蕴由于谋反被杀,而沈攸之起兵于荆州,誓与萧道成决一死战,在其前程未卜之际,卞彬居然敢直面萧道成,也就是南齐朝的开国之君,借助自己杜撰的谣谚体谜语,实际上具有“”的特点,来表达对褚渊首鼠两端之不屑,而且寄希望于沈攸之出师告捷,等到那时,恶有恶报,褚渊绝无好下场,而谋篡之主萧道成,也就是卞彬面前的这位齐高帝,则会死得更惨。甚至在刘宋大势已去的时候,卞彬还建议尚未登基的齐王萧道成“以青溪为鸿沟”,宋、齐分治,不要取代宋朝,竟敢如此放言无忌,从其文辞机敏之背后,也可以看到卞彬的铁骨铮铮与大义凛然。
当然,对于不顺从者,犹如汉光武之于冯敬通,齐高帝即使不杀他,也绝不让他有好日子过,卞彬自然陷于窘迫之中。《南史》本传记载:“后为南康郡丞。彬颇饮酒,摈弃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蚤蝨》《蜗虫》《虾蟆》等赋,皆大有指斥。其《蚤蝨赋序》曰:‘余居贫,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缊,有生所托,资其寒暑,无与易之。为人多病,起居甚疏,萦寝败絮,不能自释。兼摄性懈堕,懒事皮肤,澡刷不谨,澣沐失时,四体,加以臭秽,故苇席蓬缨之间,蚤虱猥流。淫痒渭濩,无时恕肉,探揣擭撮,日不替手。蝨有谚言:“朝生暮孙。”若吾之蝨者,无汤沐之虑,绝相吊之忧,晏聚乎久袴烂布之裳,复不懃于捕讨,孙孫子子,三十五岁焉。’其略言皆实录也。”卞彬作文,属后汉赵壹辈之流亚,愤世嫉俗,诡谲夸饰,善于哭穷。此《蚤蝨赋序》相对于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在描写自己生活邋遢方面,可谓“后来者居上”,岂止放浪形骸,不修边幅,甚至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而其人生活状况如此不堪,实际上控诉了自南齐建国以来,卞彬所遭受的迫害,这就是做前朝义士必须付出的代价!《南史》本传接着又叙述:“又为《禽兽决录》。目禽兽云:‘羊性淫而佷,猪性卑而率,鹅性顽而慠,狗性险而出。’皆指斥贵势。羊淫佷谓,谓吕文显;猪卑率,谓朱隆之;鹅顽傲,谓潘敞;狗险出,谓文度。其险诣如此。《虾蟆赋》云:‘纡青拖紫,名为蛤鱼。’世谓比令仆也。又云:‘蝌斗唯唯,群浮暗水,唯朝继夕,聿役如鬼。’比令史咨事也。文章传于闾巷。”卞彬好以家畜和家禽以及蛤蟆来比拟自己所不喜之人,虽然其天性尖刻,或好故弄玄虚,但是,以刀笔为利器,令读者可发一噱的同时,那些被卞彬所奚落的权贵,几乎猪狗不如,他们的人设就崩塌了,可以想见卞彬勇者不惧、笔力千钧!
《南史·文学列传·高爽传》云:“时有广陵高爽,博学多材。刘蒨为晋陵县,爽经途诣之,了不相接,爽甚衔之。俄而爽代蒨为县,蒨遣迎赠甚厚。爽受饷,答书云:‘高晋陵自答。’人问其所以,答云:‘刘蒨饷晋陵令耳,何关爽事。’又有人送书与爽告踬,云:‘比日守羊困苦。’爽答曰:‘守羊无食,何不货羊籴米。’孙抱为延陵县,爽又诣之,抱了无故人之怀。爽出从县阁下过,取笔书鼓云:‘徒有八尺围,腹无一寸肠,面皮如许厚,受打未讵央。’爽机悟多如此。坐事被系,作《镬鱼赋》以自况,其文甚工。后遇赦免,卒。抱东莞人。父廉,吴兴太守。抱善吏职,形体肥壮,腰带十围,爽故以此激之。”高爽性格冷僻孤傲,对于刘蒨之前倨后恭,他睚眦必报;而有人求他施以援手,他表现得十分冷漠,一毛不拔;虽愤懑于世态炎凉,可是高爽亦应反躬自问。后来孙抱对他不够礼遇,他就题字鼓上,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然而以鼓为嘲,其比喻之贴切,语辞之刻薄,亦确能令人忍俊不禁。
《南史·文学列传·仲明传》述及:“初,仲明与刘融、卞铄俱为袁粲所赏,恒在坐席。粲为丹阳尹,取铄为主簿。好诗赋,多讥刺世人,坐徙巴州。”卞铄作诗赋以讥刺世人,其作品多有评判的锋芒,可见当时以文字来讽刺丑类,几乎成为当时文坛的风气。
《宋书·谢灵运列传》云:“灵运以疾东归,而游娱宴集,以夜续昼,复为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岁,元嘉五年。灵运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长瑜文才之美,亚于惠连,雍、璿之不及也。临川王义庆招集文士,长瑜自国侍郎至平西记室参军。尝于江陵寄书与宗人何勖,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云:‘陆展染鬓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轻薄少年遂演而广之,凡厥人士,并为题目,皆加剧言苦句,其文流行。义庆大怒,白太祖除为广州所统曾城令。及义庆薨,朝士诣第叙哀,何勖谓袁淑曰:‘长瑜便可还也。’淑曰:‘国新丧宗英,未宜便以流人为念。’庐陵王绍镇寻阳,以长瑜为南中郎行参军,掌书记之任。行至板桥,遇暴风溺死。”何长瑜与宗人何勖书信中,按捺不住自己对临川王刘义庆州府僚佐某些人的轻蔑和鄙视,因此写下:“陆展染鬓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诸如此类的打油诗。而此诗所嘲讽的陆展,他染发以取悦小妾,可是青春小鸟一去不复返,苦于白发破皮而出,还是遮掩不住,此诗挖苦了老男人的烦恼。而这种嘲人之诗居然流传出去,不胫而走,轻薄少年竞相仿效,被嘲之人越来越多,成为戏谑的狂欢,这令刘义庆大怒,按周一良先生《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一文,揭示刘义庆“唯恐政治上遭猜忌”的心态(载《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刘义庆要保持低调,以免惹祸,而何长瑜不免轻佻,因而遭贬谪,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 沙场好勇斗狠之戏剧化语言两军兵戎相见,首先使用的文体是檄。南朝宋初建之时,《宋书·庾登之传》载:“晦时位高权重,朝士莫不加敬。”谢晦曾经显赫一时,宋文帝要消灭谢晦,谢晦率军抵抗,观其表、檄之类文字,按《南史·袁湛传》之《袁传》载袁子袁戬曰:“一奉表疏,便为彼臣,以臣伐君,于义不可。”可见谢晦首先上表,乃表示自己与宋文帝君臣关系尚未破裂,希望文帝赦罪。然而不获宽恕,势已无法转圜,于是发表檄文,想做最后一搏。按《文心雕龙·檄移》篇云:“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鞶鉴于已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或违之者也。”可见檄文用以表示矛盾已经激化,双方关系彻底破裂,已经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接着谢晦又上一表,这是武力抗争之余,感到力有所不逮,怀着侥幸的心理,想获取回旋余地,可是兵败如山倒,谢晦终难逃一死。虽根据《宋书·何承天传》记述,谓这些表、檄出自何承天手笔,但是亦真切地表达谢氏陷于灭顶之灾时的心声,尤其《悲人道》充分表达了谢晦人生的感慨,字字血泪,催人泪下。
从谢晦的一表,二檄,三又表,反映了檄文属于十分独特的文体,把一己的冤屈、仇恨,以及对方的罪恶滔天,罄竹难书,都要凝聚在字里行间,所追求者,乃文字的穿透力和威慑力,从而鼓舞同仇敌忾的士气。《宋书·臧质列传》记述:“二十八年正月初,焘自广陵北返,便悉力攻盱眙,就质求酒,质封溲便与之。焘怒甚,筑长围,一夜便合,开攻道,趣城东北,运东山土石填之……”南朝宋与北魏两军对垒,拓跋焘向臧质索酒,这是故意表示轻蔑的行为,而作为守方的臧质不肯示弱,竟然以屎和尿送给来犯之敌,此激怒拓跋焘,于是城外城内展开激烈的攻防之战。
《宋书·臧质列传》又云:“焘与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拓跋氏属于鲜卑族之一支,他告诉臧质,他所派遣包围盱眙城的士兵尽非鲜卑族人,他们分别属于丁零、胡及三秦氐、羌族之人,拓跋焘驰书臧质,和盘托出其险恶用心,告诉臧质乐见南军将士多多杀敌,我的目的就是借刀杀人,你所杀的那些异族兵士,正是我心腹之患,你杀此辈越多,就越助我减轻压力。借此亦可一窥北朝政局中鲜卑与其他种族之间的关系,拓跋氏如此蛇蝎心肠,若令那些浴血奋战的“非我族类”者闻见,不知会否反戈一击?
《宋书·臧质列传》又载录臧质答书曰:“‘省示,具悉奸怀。尔自恃四脚,屡犯国疆,诸如此事,不可具说……寡人受命相灭,期之白登,师行未远,尔自送死,岂容复令生全,飨有桑乾哉!但尔往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杀尔,尔由我而死。尔若有幸,得为乱兵所杀。尔若不幸,则生相剿缚,载以一驴,直送都市……粮食阙乏者告之,当出廪相饴。得所送剑刀,欲令我挥之尔身邪!’”按照《文心雕龙·檄移》篇,臧质和拓跋焘书信往还,具有檄移的特质,所以必须写得剑拔弩张,厉辞如雷,要在声势上先胜对方一筹。上述臧质的答书连用几个“死”字,震慑拓跋焘,诅咒他难逃一死,至如“载以一驴”云云,则洋溢着戏谑的气息,果然令拓跋焘大怒。于是,拓跋焘乃作铁床,于其上施铁镵,云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此番叙述,环环相扣,层层升级,到了咬牙切齿,不共戴天的地步,而书信中的文字,恰好烘托出两造几乎青筋爆裂般的虎視眈眈,故而极具戏剧效果。
《宋书·臧质列传》记录战争:“虏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虏死者与城平。又射杀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过半。”最后拓跋焘率军遁走。
这场发生在宋元嘉二十八年的南北战争湮没在古战场的尘埃之中,可是,观两军对垒主将之间互相恫吓的书信文字,既杀气腾腾,又夹杂着鄙夷的嘲弄,折射出此次鏖战的血腥和紧张,将永载史册。
三、 文士揣着明白装糊涂以耍弄同道孔子以为人分上中下三等,故有中人以上或中人以下的分别(见《论语·雍也》),正由于人的智商、情商高下不同,所以世人一直存在着嘲人和被嘲的关系。《宋书·袁淑列传》谓:“淑喜为夸诞,每为时人所嘲。始兴王浚尝送钱三万饷淑,一宿复遣追取,谓使人谬误,欲以戏淑。”始兴王浚虽然身份特殊,但也算文士,他先赠钱给袁淑,仅过一夜,则又派人去取回,令袁淑空欢喜一场。而迂腐的袁淑居然还写信给始兴王,表述对此事怏怏失望之情。当有一笔钱财自天而降,袁淑既欣喜又惊异,可惜:“弗图旦夕发咫尺之记,籍左右而请,以为胥授失旨,爰速先币。”得而复失,袁淑深感沮丧。而如此玩弄读书人的尊严,此始兴王浚所开玩笑显得恶俗、失道,在贫寒读书人情感跌宕之间,肆意地索取戏弄别人的快乐,然则此种快乐是建立在被玩弄者的痛苦之上,则会激起正人君子之厌恶!
《南齐书·周颙列传》云:“每宾友会同,颙虚席晤语,辞韵如流,听者忘倦。兼善《老》《易》,与张融相遇,辄以玄言相滞,弥日不解。清贫寡欲,终日长蔬食。虽有妻子,独处山舍,甚机辩。卫将军王俭谓颙曰:‘卿山中何所食?’颙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文惠太子问颙:‘菜食何味最胜?’颙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时何胤亦精信佛法,无妻妾。太子又问颙:‘卿精进何如何胤?’颙曰:‘三途八难,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对曰:‘周妻何肉。’其言辞应变,皆如此也……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辩。后何胤言断食生,犹欲食白鱼、脯、糖蟹,以为非见生物。疑食蚶蛎,使学生议之。学生钟岏曰:‘之就脯,骤于屈伸;蟹之将糖,躁扰弥甚。仁人用意,深怀如怛。至于车螯蚶蛎,眉目内阙,惭浑沌之奇,矿壳外缄,非金人之慎。不悴不荣,曾草木之不若;无馨无臭,与瓦砾其何算。故宜长充庖厨,永为口实。’竟陵王子良见岏议,大怒。”王俭出自琅邪王氏,属高门士族,在文化方面依然带有显而易见的自负,所以周颙与王俭和文惠太子的一问一答,就颇有点后世禅宗打机锋的意味,周颙文辞之清丽,可谓唯美之至,给人以美的遐想。然而,过犹不及,太学诸生也来模仿此种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其中一位钟岏善插科打诨,对于何胤既言不沾荤腥,却嗜食海鲜,深感其虚伪,便发议论,进行辛辣的讽刺。而何胤靠拢文惠太子和竟陵王萧子良,他们几乎是一个佛学的集结,因此,对于钟岏的出言不逊,就令竟陵王子良大怒。然而,从此间也可以看见,使用文字和语词,营造文人趣味,亦是民族固有的幽默文化传统。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云:“吾见世人,至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痴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赋,撆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妇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所记人物故事虽在北方并州,可是颜之推一生主要居住于南方,此节文字亦可视为南人之视北人,此北人之趣事,在南人眼里,更平添几分喜剧色彩,而且将这位并无文学才华,却自视甚高的并州士族的可笑行径,冠以江南“痴符”的戏称,亦凸显了令人掩口胡卢而笑的人物情节与声口,在每一个时代,这样的文学青年似乎都不会绝迹。
四、 借女性之口以表达女性的平等意识中国女性长期受男性性别优势欺压,她们经常身不由己,听人摆布,犹如待宰羔羊,如何体恤女性悲惨处境,除了男子怜香惜玉之余,女子在某些語境中,竟然也会对同性者产生恻隐之心,这亦堪称另一种形式的“反身而诚”。《世说新语·贤媛》第二十一条刘孝标注引《妒记》曰:“(桓)温平蜀,以李势女为妾,郡主凶妒,不即知之。后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见李在窗前梳头,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悽惋。主于是掷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本来郡主是带着一肚皮的醋意和愤恨,要严惩桓温的新宠,竟然拔刀而往,其怒不可抑的凶相跃然纸上,但是,当她看到此位被丈夫金屋藏娇的美女,姿貌端丽,神色姿态楚楚动人,此种完美的女性,几乎达到了女神的境界,她忽然顿悟,自家男人喜欢她,那是自然而然的,是不可阻挡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因此,一腔妒火和杀气突然转变成审美意识,情不自禁地说出,我见到你都会喜欢上你,何况我家老头了!此种戏剧化的逆转,大致非写实性叙述,更多出自男性作者的想象和演绎,却令读者舌挢不下,对这位郡主也产生一丝敬意。
吴士鉴、刘承干撰《晋书斠注》卷七十九《谢安列传》注引《御览》五百二十一《妒记》曰:“谢太傅刘夫人不令太傅有别房宠。公既深好声色,不能令节,遂颇欲立妓妾,兄子及外甥等微达其旨,乃共谏刘夫人,方便称《关雎》《螽斯》有不嫉妒之德,夫人知讽己,乃问谁撰诗,答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为耳。若使周姥传,应无此语也。’”谢安这位刘夫人颇具慧根,充满了思辨能力,不经意间,就点穿了文学甚至整个文化中所弥漫的男性主宰意识,她堪称是女性平权思想的先驱!
在中华民族充满艰辛的历史进程中,唯有幽默,令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除了眼泪之外,还有欢笑。因此,幽默是弥足珍贵的民族性格,需要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