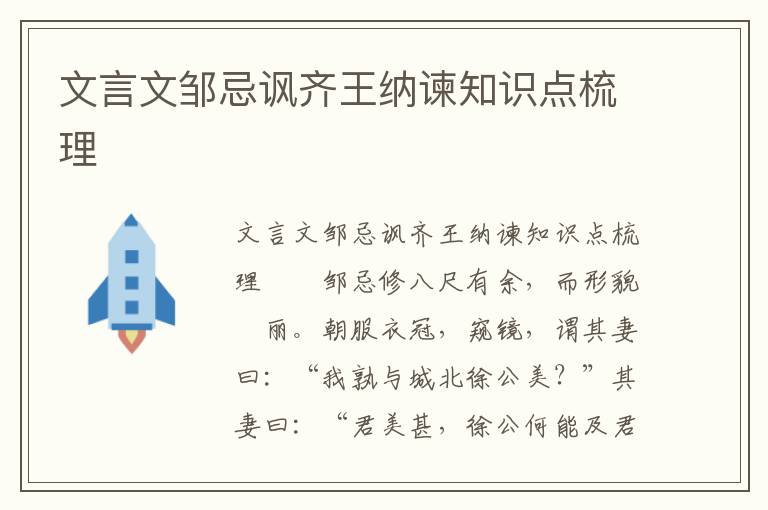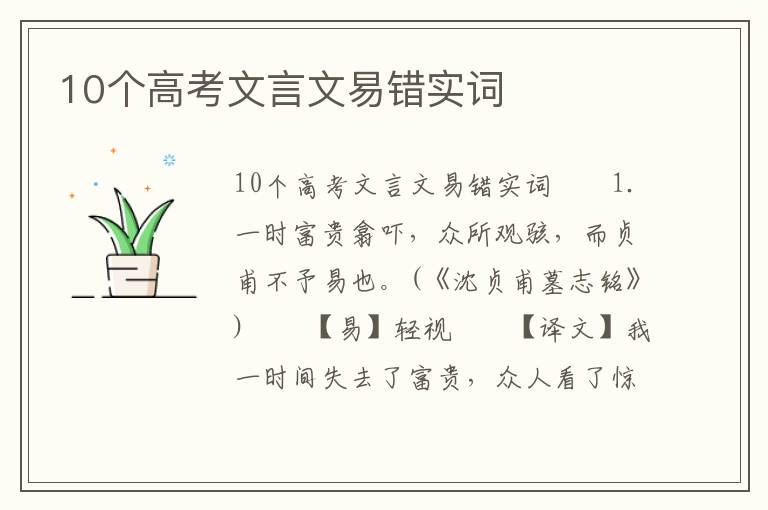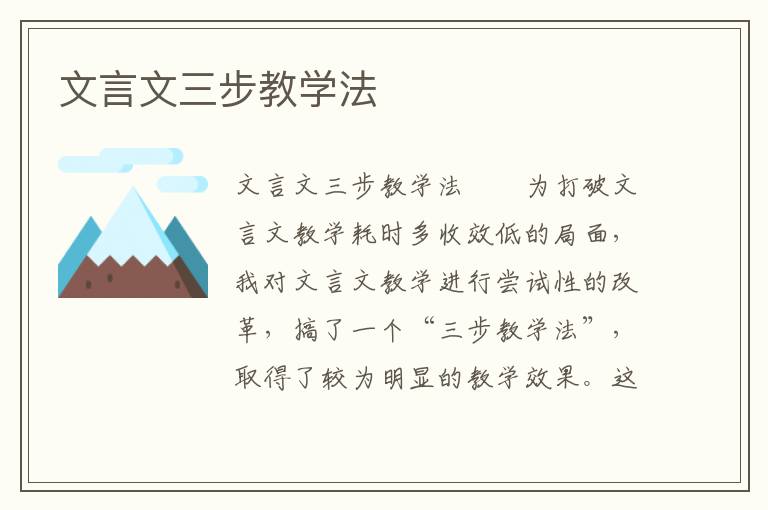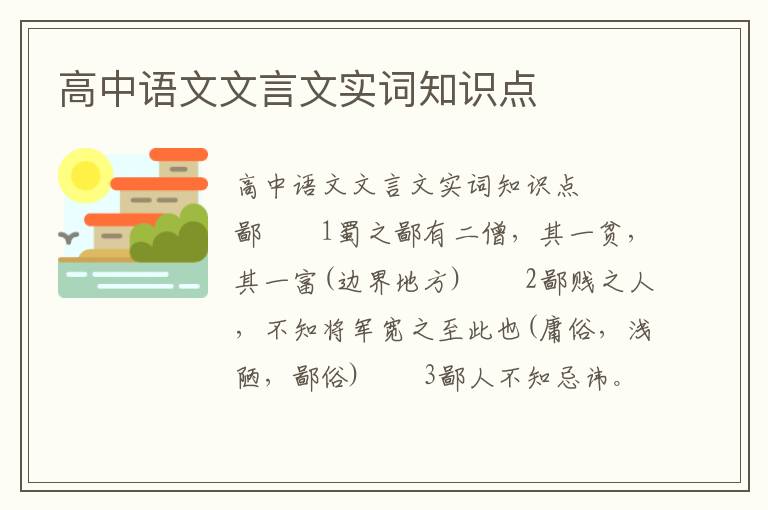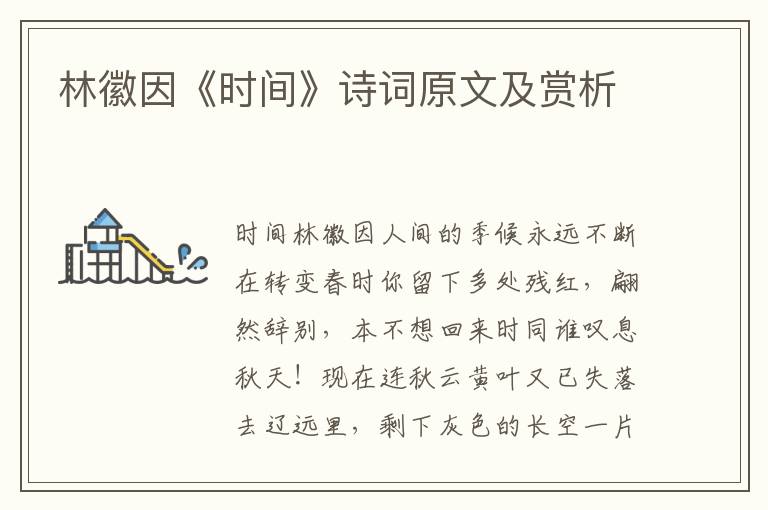【简介】感谢网友“雕龙文库”参与投稿,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方便大家学习。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名句的诞生
红酥手1、黄滕酒2,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3。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浥红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4!莫!莫!
——陆游·钗头凤
完全读懂名句
1红酥手:形容手的红润白嫩。2黄滕酒:酒名,即黄封酒。一说即藤黄,形容酒的颜色。3索:散。4莫:罢、休,表示绝望。
记忆里,她那红润细嫩的双手,正提着黄封美酒。遥想那时,满城尽是迷人的春色,杨柳依依,傍着一大片宫墙。岂料无情的东风,吹散了两情的缱绻,理不清的一腔愁怀,只空自忆念着别后数载的离情萧索。真是错了!错了!但我又能挽回些什么?
春日一如以往明朗,人却较昨日显得消瘦。我不禁泪如泉涌,沾湿了红色手绢。桃花被春风吹落,阁畔池边闲静无人。从前两人山盟海誓虽犹在,但如今却连寄封书信、捎个讯息问问你还好吗的机会都没有。真是罢了!罢了!说不出口的相思已成空。
词人背景小常识
陆游(公元1125—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陆游刚刚出生时,母亲在前一晚梦到了秦观(字少游)——苏门四学士、六君子之一,北宋的大词人;而十分凑巧的,陆游的外婆是晁家人,而晁补之亦是苏门六君子之一,这么一牵扯,陆游似乎也和秦观有些关系,便是因为这个缘故,陆游名“游”,字“务观”。
陆游渐渐长大,他的才华也慢慢显露出来。他12岁时便能诗能文,到了十七八岁,就跟当时一些有名的文人交游,文名远播。陆游在18岁时到临安去应试,在省试时遇到当时宰相秦桧的孙子秦埙也来应试,主试官陈子茂不顾上层的压力,给了陆游第一名。到了次年殿试,秦桧的威权起了作用,又因为陆游“喜论恢复”,竟被除名。
但是,具有浪漫特质的陆游从没放弃任何一丝希望,他当然也有“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悲痛,但即使在一片主和、投降声中,他还是坚持抗战,随时准备出击,并期盼着成功的到来。陆游到了80岁,还到临安再次参与抗敌的行动;84岁时,陆游在病榻上,顾念的只是国家;双方的作战,关中的收复,这一切都记录在他病中的诗稿里。
85岁那年,陆游在病榻上瞑目了。临终前,他没有其他交代,只写下了一首《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名句的故事
一切要从陆游的婚姻说起。
大约在20岁左右,陆游和唐琬结婚。唐琬和陆游有亲戚关系,偏偏陆母对这一位媳妇非常不满,甚至逼迫陆游,要他们离婚。在当时的封建社会,谁敢违父母的命令?不久之后,陆游和王氏结婚,唐琬也改嫁赵士程。
一晃眼,七年多的岁月很快就过去了,陆游已是而立之年,但对唐琬的思恋之情却不随时间而消损。有一天,陆游到沈园游览,恰巧赵唐夫妇也到那里。虽然是长久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但是千言万语从何说起?他们会面了,又分离。陆游无语伤神,就在这时,一个小二送了酒菜过来,一问之下,原来是赵士程吩咐的。陆游恍然失神,沉默了半晌,酒冷了,菜肴也冷了,于是他把眼泪和酒一起咽下,对着面前的粉墙,题下了这阕词。
词文一开头即写出唐琬把盏的动人丽致,后来便诉说着两人被迫拆散的痛苦和离愁。“一怀愁绪”二句,则总结词意,写出了陆游几年来的哀愁。上片最后以三个“错”字结尾,表达了陆游强烈的悔恨之情。两人的分离,错了!真是错了!但陆游能违逆母令吗?他还能挽回些什么?
据说唐琬看到了这阕词,难过不已,后来也和了一阕。但因为过度伤心,不久之后便死了。
虽然陆、唐两人不过维持了两三年的婚姻,但彼此用情很深。陆游一直到晚年,对于唐琬依旧是无限思念。75岁时,他写下这样的诗句:“城上斜阳画角哀,沉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沈园》)其中的“惊鸿照影”、“梦断香消”,都是对唐琬的形容。这样的爱情,这样的诗句词句,将永远流传下去,而为后人所传诵称道。
历久弥新说名句
说到夫妻间的爱情,会想到唐朝诗人王维;他30岁时妻子便去世了,之后一直到死,历时30年,王维都未曾续娶。也因为丧妻以及母亲的因素,王维后来就屏绝红尘,不问世俗,潜心奉佛。
再看到唐朝另一位文人元稹,他对妻子韦氏也是十分爱恋,韦氏死后,他曾写了《遣悲怀》诗三首表达对她的怀念,其中“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
从元稹到陆游,诗人骚客多愁善感,自是多情,那力求精确、实事求是的科学家,对于他的另一半是否也是如此眷恋呢?且看看电学之父法拉第和他的妻子的故事。
对于法拉第的伟大之处,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他一生致力于发展电磁学,人类史上第一部发电机便是他的发明。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法拉第,就没有现在的电机工程学。而“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辛苦的女人”,那个女人便是他的妻子。
1861年,法拉第自服务49年的皇家科学院退休,退休之后,他仍继续不断他的研究,一直到1865年,他在皇家科学院发表最后一次演讲中感谢他的妻子撒拉:“她,是我一生第一个爱,也是最后的爱。她让我年轻时最灿烂的梦想得以实现;她让我年老时仍得安慰。每一天的相处,都是淡淡的喜悦;每一个时刻,她仍是我的顾念。有她,我的一生没有遗憾。我唯一的挂念是,当我离开之后,一生相顾、相爱的同伴,如何能忍受折翼之痛,我只能用一颗单纯的心,向那永生的上帝祈求:‘我没有留下什么给她,但我不害怕,我知道,你一定会照顾她,你一定会照顾她!’”(参考自张文亮《法拉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