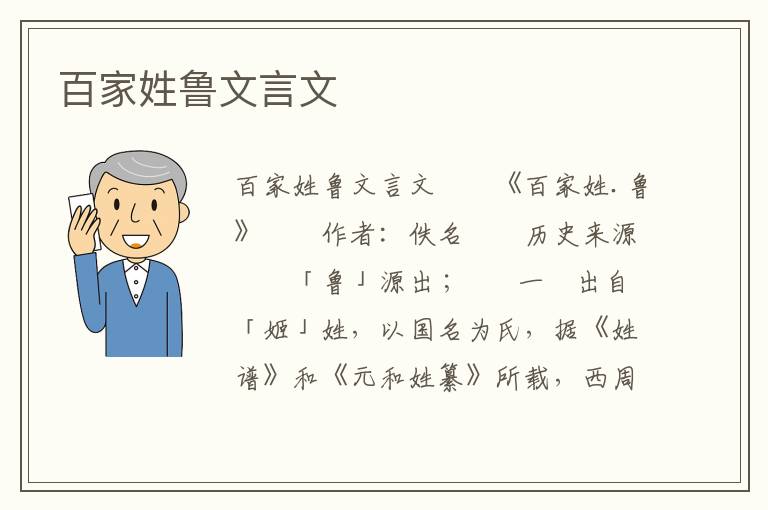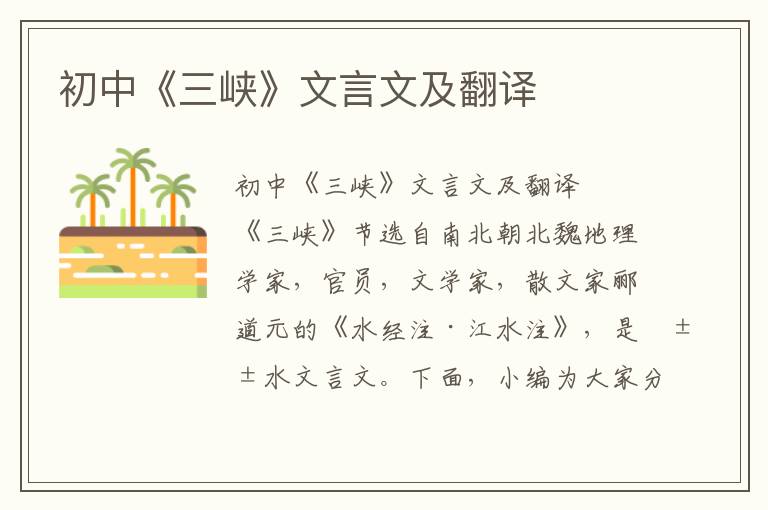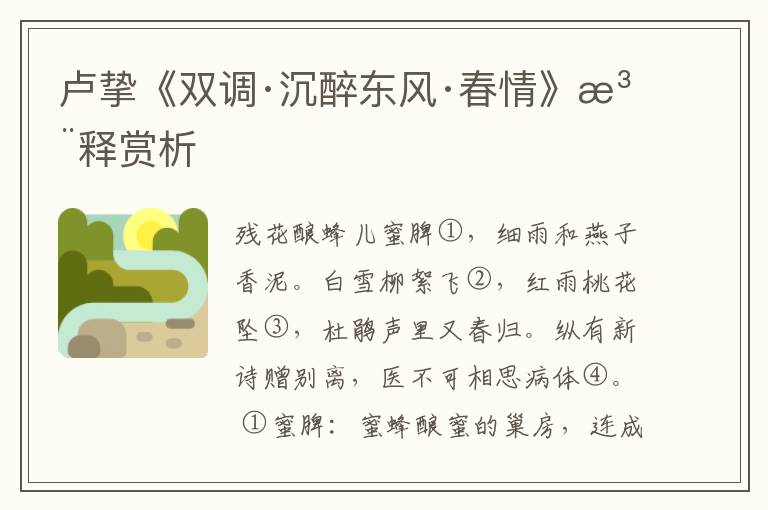【简介】感谢网友“雕龙文库”参与投稿,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方便大家学习。
此图为清代冷枚所作《春闺倦读图》,现藏天津博物馆。冷枚,字吉臣,胶州人。清代康熙年间供奉内廷,工人物,尤工仕女。翁方纲有诗《冷枚画》:“冷枚法本西洋派,多在轻烘淡染中。始识曹吴工一变,衣纹出水带当风。”(《复初斋外集》诗卷第十二)诗中所言,冷枚画法受到西洋画家的影响,所指乃康熙年间宫廷画家郎世宁等所擅长的透视等法。清人王培荀称曾见冷枚画美女坐像,尺寸如真人,又称“美人小者易工,大者最难”(《乡园忆旧录》卷一)。
可见此种美人画并不易作,而冷枚所画仕女,时人评如工丽妍雅、笔墨洁净、赋色韶秀,屋宇器皿精细如界画,生动有致云云(清·秦祖永《桐阴论画三编》上卷)。
由此画之细节可见一斑,学界对其亦多有讨论。本文旨在完善其中一个小问题,即画中美人手持之书。图中可见桌案上有一蓝色书匣,上题三字乃“媛诗归”,是则美人所持书为《名媛诗归》其中一册当无疑问。
手中书卷显示的文字在《名媛诗归》卷三最末。“子夜”题下小字云:“子夜,晋女子也。尝造曲,声过哀苦,因有四时行乐之词,谓之子夜四时歌。”
第一首原文为:
芳是香所为,冶容不敢当。天不夺人愿,故使侬见郎。
诗句后的双行小字为谭友夏评语。“芳是香所为”后为“谭友夏云香奁中入细佳语”。“冶容不敢当”后为“谦得不情妙”。后一句末为“谭友夏云感天妙。感天只在不夺人愿,感得痴”。此诗末还有一句总评:“谭友夏云女郎有极夸口语,有极谦让语,总之,遇有情人,夸口亦妙,谦让亦妙。”
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中《子夜歌》为四十二首。诗前有解题:《唐书·乐志》曰“子夜歌者,晋曲也。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声过哀苦”。《宋书·乐志》曰“晋孝武太元中,琅琊王轲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为豫章,豫章侨人庾僧虔家,亦有鬼歌《子夜》”。《古今乐录》曰:“凡歌曲终,皆有送声。《子夜》以持子送曲,《凤将雏》以泽雉送曲。”《乐府解题》曰:“后人更为四时行乐之词,谓之《子夜四时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变歌》,皆曲之变也。”可以看出《名媛诗归》在辑录《子夜歌》解题时有所删节,诗文亦仅录二十七首。
画中所呈现的诗文是女子的应答。她所应答的是《名媛诗归》中没有收录的《子夜歌》原本的第一首:“落日出门前,瞻瞩见子度。冶容多姿鬓,芳香已盈路。”这句诗既写了女子为见心上人精心装扮,使自己在落日余晖的光泽中充满迷人的芬芳,又写了被美色吸引的男主人公因忘情而失礼的心迹表达。用“冶容”形容所见到的女子,其意味不言而喻:《周易·系辞》“冶容诲淫”;《抱朴子·内篇》“冶容媚姿,铅华素质,伐命者也”。女子的回应则显得退让、有分寸,她明白“冶容”二字背后潜藏的渴望,“不敢当”三字,说明心里不愿意接受这种“不尊重”的恭维。虽然心中有所失望,但还是希望见到心上人,后两句诗带有爱情开始时特有的明快。然而《子夜歌》毕竟是哀苦的,这首诗的选择暗含着凄苦的基调。
此画的背景中有一小幅山水,这一“画中画”的落款是“甲辰冬日画,冷枚”。甲辰乃雍正二年(1724),据聂崇正先生考证此时冷枚已经不供奉内廷,颇有失宠之嫌(见《清宫廷画家冷枚其人其作品》)。而这幅画描绘的是山水间一位渔翁独自垂钓,隐隐有作者乃世外高人的自况意味。虽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冷枚与《胤禛围屏美人图》的创作有关,但是两幅读书图中却出现了同样的一部书,只是所选取的诗文内容不同。这从一个微观的角度表明《名媛诗归》及其所代表的明清之际的才媛文化在此类绘画题材中的影响。
在冷枚的画作中,《名媛诗归》作为书籍的细节展示得更为明确。这说明冷枚作品中的书籍不仅具有文本内容层面的意义,还附带着书籍本身的表意功能。图像中书籍内容的明确呈现,并不仅仅意味着细致入微的写实性,而且表明它是画面表达意蕴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高居翰先生的研究认为冷枚选择的诗歌文本以及他在画面中塑造的带有挑逗意味的美人姿态,表明这属于一类从男性视角出发而创作的仕女图像(见《明清时期为女性而作的绘画?》)。
由此出发,研究者对此图中的女性身份是大家闺秀还是风尘名媛亦产生了分歧。可见在这一类型的美人像中,画中人的身份是难以确定的,但是她身处的布置典雅的室内环境尤其是正在阅读的书籍,表明她具有艺术修养,特别是诗词方面的造诣。与真实身份相比,藉由书名乃至书页上精心选择的内容所传达出的意蕴应该才是作者的匠心所在。尽管此类诗歌内容不外乎对意中人的思念,但是并不能直白地将其意图归类为对观者的诱惑尤其是对男性观者的取悦。《名媛诗归》作为女性诗歌选集在图像中的明确呈现,诠释出画作者想要展现女性才情风貌的意图。
今日流传的冷枚所作仕女图中还有两幅与“读书”有关,不妨将之解读为第二种类型,即读书作为画面表现的主题。现藏中央美术学院的《蕉荫读书图》和另一幅藏地不详的《仕女图》之间,整体布局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以至于有研究者認为这是同一构思下的不同稿本。画面中女子所读之书只画了行格,没有内容,说明作者不需要借助文字的功能来申发画面的内涵,只是想要呈现此种正在阅读的姿态。如果仅从这种姿态来看,虽然两幅画展现了几乎相同的室外阅读空间,然而“个人阅读”和“同伴共读”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阅读感受终究还是使两幅画传达出大相径庭的氛围。前者显得更为怡情和诗意,后者则带有狎昵的亲密感。当然,无论从构图还是从内蕴来看,此类“美人读书”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因袭意味,我们可以从明清之际的仕女图中找出不少例证,此处暂不赘言。
大英博物馆藏有另一幅冷枚所作《仕女图》,图中人的坐榻上摆放着书函,这仍是一整套书,但是画中人没有捧读,而是将其中一册倒扣在案,一手托腮作遐思状。这让我们无从得知书的内容,仅能体会到画中人是因读书而沉思。这幅画构图简明、色调独特,与之前室内、室外两种巨细靡遗的场景铺陈截然不同,似乎可以称作冷枚所作美人读书像的第三种形式。如果说前两种形式体现了冷枚在创作仕女画的过程中因袭和借鉴的一面,那么此种形式的仕女图则更多地成为他人借鉴的对象。清道光年间改琦所作的《元机诗意图》即是最好的例证。
改琦(1773—1828),字伯蕴,号香白,又号七芗、玉壶山人,松江人,工山水、人物、折枝花卉,亦善诗文词及小楷。其所绘仕女图落墨洁净,设色妍雅,名擅一时,号为“改派”,其作品最为世人所知者乃《红楼梦图咏》五十幅。改琦交游遍及江南名士,此图名《元机诗意》,是为当时著名藏书家黄丕烈而作。黄丕烈藏有宋本《唐女郎鱼玄机诗集》,曾为赏鉴此书举行诗会。改琦之作原图有题曰:“秋室老人有此图,今在荛圃处,乙酉初夏七芗改琦并记。”乙酉为道光五年(1825),此图作于初夏,作于黄丕烈的第二次咏鱼玄机诗集的集会之前。
黄丕烈的重要藏书都伴随着“得书图”的征集,即延请当时的著名画家以其所得之书为题作画。改琦比黄丕烈小十岁,现留存的有关二人之间交往的记载很少,但很可能是以征集“得书图”为契机的。黄丕烈曾在一幅改琦的画卷中作跋谈到《得书图》的事情(此跋见韦力、拓晓堂:《古书之媒:感知拍卖二十年摭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辛未春分日,改君七香偕古倪园主人访余于陶陶室,携此卷相示。余素不识画而却喜画,余倩诸友人画得书图已有三十六幅矣,兹又将乞七香为之。
七香知余藏《古列女传》,其画为古,佩服而欲观之以进于古,乃先示余《云山无画卷》,余亦何幸而得见所未见耶?卷中有歙汪梅鼎看款,浣云余友也,《续得书十二图》即其所作,中有一图云《云山江水》,颇极笔墨之妙,然其跋云“只画钓台一角”,恐不能如此之无画也。请还以质诸七香之善画者。
此跋所记之事在嘉庆十六年(1811)辛未春分日,改琦与古倪园主人沈恕同访黄丕烈,其缘由是改琦希望一睹黄丕烈所藏之《古列女传》。因改琦专攻仕女画,故欲观此书中之图。沈恕曾以黄丕烈藏本刊刻过《四妇人集》,他应该对黄丕烈此类藏书非常熟悉,同时,也对黄丕烈广征得书图的情况非常了解,所以他很可能是以一位中间人的身份陪同改琦前来。改琦带了一幅自己的画作请黄丕烈作跋,此画虽然不是仕女图,而是一幅山水画,但上面有黄丕烈友人汪浣云的观款,这让黄丕烈立刻联想到自己的得书图(此时已有三十六幅之多),他当即表示也请改琦为自己的“得书图”再添佳构。那么我们不妨展开想象,黄丕烈会邀请改琦为自己的哪部书作画呢?无论从画家的专长(仕女)、此次造访的目的(看《古列女传》)、此行的陪同者(刊行了《四妇人集》的沈恕)来看,此情景之下,《唐女郎鱼玄机诗》都应该是黄丕烈会立刻想到的那部书。然而,改琦的《元机诗意》与此次过访相隔了十余年。据道光五年鱼集集会的参与者陈彬华称,《元机诗意》作成后曾悬挂于百宋一廛(见陈彬华题诗自注,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卷五,民国上海蟫隐庐石印本)。
改琦画成之日在初夏,集会在七夕,时间相隔很近,故此画之交付、悬挂与赏玩,也有可能成为七夕以鱼集集会的一个因由。
改琦题中所称“秋室老人”指余集,是黄丕烈的友人,也是当时著名的仕女画家,他所作的鱼玄机画像被黄丕烈装裱于宋本《唐女郎鱼玄机诗》卷首。
余集所作之图名为《唐女道士鱼元机小影》,此图完全采用白描手法,鱼玄机身着道衣,手持一柄如意,体态丰腴,面如满月,皆欲表现审美印象中的唐代女子之美貌。而改琦所作之《元机诗意》,从画面构思上则承袭冷枚《仕女图》。从画面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改琦的笔意:鱼玄机手持书卷,身着道袍,扶坐于椅上,表明其道士与诗人的双重身份。显然,改琦笔下的鱼玄机眉目神情更趋近于清人审美,并没有像余集那样刻意表现唐人丰腴之貌。此外,改琦还注意改变了一个书的细节,鱼玄机手中所持类似卷子,符合唐代书籍常见的卷轴形式,而非冷枚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明清时期所见之书籍装帧。
女诗人作为美人画的表现题材至少在明代末期已很流行,如徐作有《题画美人》十四首,其中咏鱼玄机诗云:“霞帔云衣莲叶冠,有时持咒下瑤坛。手中玉轴三千卷,不写春情寄子安。”虽画已不传,但是从题诗可以看出画中鱼玄机是以道衣为装扮、手持玉轴卷子,与改琦笔意相似。可见改琦的《元机诗意》无论从画面构图亦或表现方式,仍与明清以来纷呈的美人画像一脉相延。
从冷枚以一部《名媛诗归》构建清代女性的阅读场景,到改琦以一幅《元机诗意》为当时的书籍赏鉴活动添助风雅,不难看出美人读书图景中诗意传达的两个维度:当下生活里不愿具名的闺秀因阅读著名诗集具有了诗思和诗才的内在指向,而历史上著名的女诗人无须展卷就已经使观者对画中的无字之书充满遐思。此二者之间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读书姿态,明清以来真实存在过的、情思延绵的女性藉此保留了生活的片刻诗情。那些或清晰或含混、或端正或散落的书籍所营造出的读书意境构成了中国古代仕女图像中一类既具有当下的世俗意味,又含有悠远的诗化涵义的美好图景。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