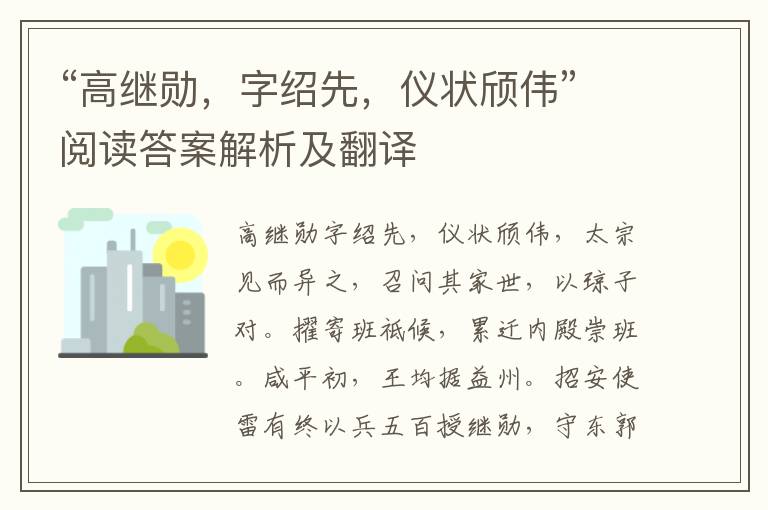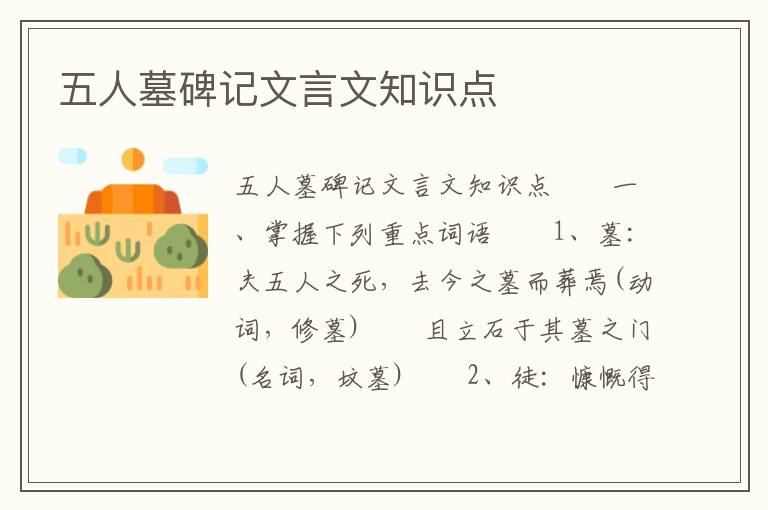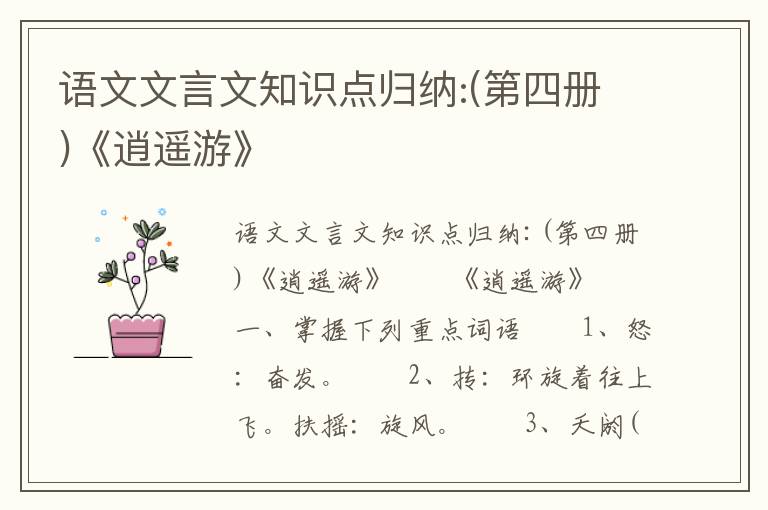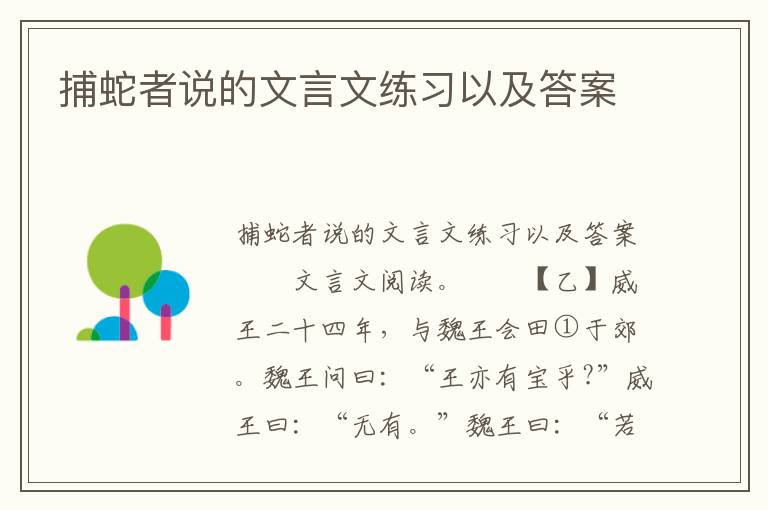【简介】感谢网友“雕龙文库”参与投稿,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方便大家学习。
曹植诗文的整理本,今以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最为通行。《校注》收入《七步诗》,注云:“案此故实已见于六朝文中,如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有句云‘陈思见称于七步’,似不能以本集不载,即云出于附会而删之,应存疑。”其意是不宜因曹植本集不载此诗而不录,不妨以“存疑”的态度收在集子里。道理是不错,问题在于既然“本集不载”,便有必要对《七步诗》入集情况作一番认真的梳理。理由是传世曹植集的早期版本,宋本《曹子建文集》(清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现藏上海图书馆)和明活字本均未载《七步诗》,这为考察《七步诗》的真伪提供了直接的实物版本依据。再者,唐李善注《文选》亦引及本集,也提供了唐本曹植集是否载有此诗的文献佐证。《七步诗》是否需要辑入本集,要重视存在的“本集不载”现象。
黄永年先生在九十年代初撰写考证《七步诗》的文章(《曹子建集二题》,载《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指出清卓尔堪编《合刻曹陶谢三家诗》最早否定《七步诗》为曹植作,称誉为:“有见解,有断制。”兹检清康熙刻本卓编《三家诗》(国家图书馆藏本,编目书号13548),其中《曹集》卷一载此诗,云:“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向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题下有小注称:“本集不载。”诗末有校语称:“萁向一作萁在,釜下一作釜中。”评云:“七步者,言子建尝七步而能诗成,犹八叉手之谓,魏文岂有诗不成而行大法之理?此诗亦尝时以煮豆起兴者,非对其暴戾之兄而敢作此语。《世说新语》亦齐谐之余,小说之祖,因此诗‘同根’‘相煎’,似对其兄语,以七步附会之耳。煮豆然豆萁,亦非子建口气。”算是将此问题说得比较清楚了,《校注》不应忽视。其实卓氏也并非首发此论者,明人冯惟讷编《古诗纪》(据明嘉靖三十八年冯惟讷自刻本)之《魏诗纪》卷四所载此诗,诗题下已注称“本集不载”。恐怕卓氏依据的正是《古诗纪》,只是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考虑到宋本毕竟不易于经见,故冯惟讷、卓尔堪所称之“本集”应该指的就是明活字本。按明正德五年(1510)田澜序(载明舒贞刻本《陈思王集》)称:“往岁过长洲,得徐氏《子建集》百部,行且卖之无余矣……盖彼活字板初有数,而今不可得也。”徐氏《子建集》即此明活字本,推断曾印卖较盛,是明人读曹植集的重要版本。
宋本不载《七步诗》,说明宋人还没有将它视为曹植的作品而入集。但宋本曹植集毕竟是北宋初的重编本,而非六朝旧集,甚至可靠性还比不上唐代流传的曹植集。按《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曹植集有三十卷本和二十卷本两种版本,其中三十卷本即《隋志》著录本。笔者在《曹植集研究三题》(载《许昌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中,已考证今宋十卷本祖出唐二十卷本,而李善注《文选》所引的曹植集属三十卷本,而且还属曹植自编全集本系统。那么唐本曹植集中是否收《七步诗》呢?有理由相信,祖出唐二十卷本的今宋本不收《七步诗》,同样也符合唐二十卷本。至于三十卷本,李善凡引此本中的曹植诗文皆径引篇题(引曹植集中之注则称“《集》曰”云云),不再赘称《集》。而注《文选》卷六十《齐竟陵文宣王行状》“陈思见称于七步”句,却引《世说》云:“魏文帝令陈思王七步成诗,诗曰:萁在灶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表明李善依据的曹植自编集中没有《七步诗》,只能引最早载该诗的《世说新语》作注。同样,《初学记》(据明嘉靖十年锡山安国桂坡馆刻本)卷十“中宫部”引刘义庆《世说》云:“魏文帝令东阿王七步成诗,不成将行大法,遂作诗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大有惭色。”又敦煌P.2524《语对》残卷云:“陈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文忌之……帝命令七步成诗,若不成,将诛王,应声曰: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并何乃急。帝善之。”虽未标注出处,但引自《世说》似无疑问。印证唐初人看到的《七步诗》都是出自《世说新语》,而非曹植集。按《世说新语·文学》(据明嘉靖十四年袁氏嘉趣堂刻本)载曹植作《七步诗》,云:“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疑脱‘豉’字)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上述唐人所引三例均由六句体易为四句体。
唐宋時的曹植集都没有收录《七步诗》,出现在集子里最早是明正德五年(1510)舒贞刻本。舒贞本有正德五年田澜序称“《七步诗》散见诸书”,遂辑入本集,收在卷九末题“《七步诗》附”。“附”字可以看出态度还是很老实的,表明这首诗本不在集,而是据它书附入其中。但舒贞本之后的明嘉靖二十年(1541)胡缵宗刻本、嘉靖二十一年(1542)郭云鹏刻本和万历三十一年(1603)郑士豪刻本,均将“附”字删掉,堂而皇之地作为曹植本人的作品。是明人将《七步诗》落实为曹植的作品,而曹植集通行本的面貌恰好又是明人建构的,遂造成《七步诗》真伪问题的分歧。故雍国泰先生称:“在目前流传的《曹集》中,即使载有《七步诗》的本子,也不能断然加以肯定。”(《七步诗与曹植》,载《四川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甚为通达!该文比黄文发表早一年,九十年代初之所以如此引起学界的注意,与八十年代出版《校注》还是有很大关系的。中华书局2016年新版《曹植集校注》载赵振铎先生《再版后记》,称八十年代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载其父(即《校注》作者赵幼文)之语云:“书出版了,有人写文章评论,说明它有社会影响,应该是一件好事。论文里面有一些意见值得重视,下次再版时应该考虑采纳。”这件事提示基本典籍的整理工作,还是能够促发针对某些问题的商榷争鸣和深入思考。可以说,以文献整理来带动学术问题的工作方式,应该成为当下文史研究中突破瓶颈的重要途径。
话再回到《七步诗》的问题。《世说新语》创造的《七步诗》文本,据任昉“陈思见称于七步”似乎在南朝齐梁时已流传开来。但南朝同时也有曹植集的流传,有本集作为依据,人们不必担心真的会“挂在”曹植的头上,也不觉得这样做有何不妥。另外卓氏所言:“《世说新语》亦齐谐之余,小说之祖,因此诗‘同根’‘相煎’,似对其兄语,以七步附会之耳。”很有启发性!说明考察曹植的《七步诗》,不要仅局限于经典层面的文献典籍(《世说新语》及据之转引的典籍),还要注重世俗层面的通俗记载。因为,自《世说新语》之后,曹植形象逐渐成为小说家言演义的重要素材,甚至还渗透到俗文化的层面,导致《七步诗》的情节及文字面貌也相应变化。李小荣老师有篇文章《七步诗生成流播过程中的佛教因素》(载《古典文学知识》2016年第6期),提及晚唐栖复撰《法华经玄赞要集》卷二十称引《七步诗》,云:
问:此方因何有梵呗?答:疏陈思等。按《历帝纪》云:魏文帝曹丕是魏武帝操之子,在位七年。武帝有二子,[一]号曹丕,二名曹植字子建。况(兄)曹丕主,封弟曹植为陈思王。陈思,郡名也,美貌有文,兄丕每礼重。偏置甄[妃]一阁,[植]遂被甄妃。后凌逼不从,自啮其臂。德困沐发,兄见妃后臂啮损,问得事由,便欲杀之。令行七步,诗成即不煞,如不成即煞。诗曰:煮豆然豆〔以〕其(萁),豆在釜中治。一种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既成已,遂免煞之,除为何(河)东候(侯)也。
印证晚唐时《七步诗》便进入佛教僧徒面向公众的经义宣解中,直接因素是曹植与梵呗的密切关系。至于曹植与甄妃事则纯属小说家言,虚构出不同于《世说新语》的另一情节。作诗字句也存在讹字,带有明显的世俗文化印迹,反映的正是《七步诗》脱离经典文本界域而进入世俗流传中出现的变异和改造。李小荣老师还提及唐咸通间人陈盖注胡曾《咏史诗》,云:“魏文帝立,乃欲诛之。公子!公子!乃何作双陆?初进之,帝方令七步作诗,乃免其诛。诗曰: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一种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遂免罪。初,为太后怜爱公子,文帝欲杀,白于太后。太后:吾不意此子若是!此乃由汝国法也!后乃免死。”双陆是皇权的象征,曹植作双陆意味着觊觎帝位之争,而不为曹丕所容。当然这同样是小说家言,情节虚构与《世说新语》和《法华经玄赞要集》则又不同。且与《法华经玄赞要集》所引《七步诗》相较,均作“一种同根生”,与传世本大都作“本是同根生”差异明显。藉此还原出的晚唐通俗世界中所传《七步诗》面貌,与经典文本很不同,呈现出经典与世俗并行不悖的两种界面态。而据考证作于北宋初的旧题唐柳宗元撰《龙城录》,尽管并未提及《七步诗》,却也记载了有关曹植的故事,云:“韩仲卿(即韩愈之父)日梦一乌帻少年,风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邺李氏。公当名出一时,肯为我讨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阴报尔。仲卿诺之,去复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检邺中书得子建集,分为十卷,异而序之,即仲卿作也。”之所以再引此条记载,是想说明大概中唐之后民间开始大量涌现以曹植为原型的逸事,而作为最有“噱头”的《七步诗》自然成为编造这些逸事的主要素材。而这些记载相较于经典文献(即《世说新语》及据之转引的典籍),有着明显的通俗性。
而改造最著者恐怕要属《太平广记》(据明嘉靖四十五年谈恺刻本)。书中卷一百七十三《俊辩》“曹植”条云:“魏文帝尝与陈思王植同辇出游,逢见两牛在墙间斗,一牛不如,坠井而死。诏令赋死牛诗,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斗,不得言其死。走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尽不成,加斩刑。子建策马而驰,既揽笔赋曰:两肉齐道行,头上戴横骨。行至土头,峍起相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赋成,步犹未竟,重作三十言自愍诗云: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世记》。”同卷“边文礼”条和“荀慈明”条均注明出自《世说》,证与《世记》似并非同书。相较于《世说新语》不仅文字有差异,情节也很不同,还是有别于甄妃、双陆的又一情节。很难确定这则情节源自何时,但大致应也产生在晚唐五代北宋初这个时段内,再次印证曹植形象集中世俗化、故事化发生在此时期。在此过程中,着眼于情节的需要而不断移植、改造既有的《七步诗》面貌,从而造成其文本“变动不居”的现象。
《世说新语》本具备小说家言的特点,特别是营造的《七步诗》情节。但由于文人的垂愛和推崇,本身已跃居经典文献的“行列”。因此凡是经典性层面典籍中的《七步诗》,均祖出《世说新语》,而保持着大致的稳定性。而在通俗性层面,故事情节演义的需要则赋予《七步诗》更多的文本表现面貌。具体到《七步诗》进入曹植集之前的时代,由于《集》中根本就不存在《七步诗》,故不管《七步诗》在通俗世界如何变花样,都不会视为曹植本人的“真实”作品。况且着眼于通俗化需要,而构建出来情节本是小说家言的虚构,心知肚明,也就更不需要有所“忌惮”了。归根结底,还在于有“权威”定本曹植集作为约束。通过经典和通俗两层面的梳理,可以清楚《七步诗》多种变化的根源在于《世说新语》赋予的虚构性;而在曹植集呈现出的真实文本世界中,《七步诗》不过是一首压根不属于本集的“集外诗”。明人重编六朝人集存在尚博倾向,其用心是良好的,目的是将相关的资料尽可能一网打尽。但也因“务得贪多”而“失于限断”(《四库全书总目》之语),导致一些伪作混入其中。后人不察,不做版本源流层面的文献甄辨,很容易将之作为凭信的依据。职是之故,《校注》不宜将《七步诗》置于正文之中,完全可以视为伪作,最多也只是列在“附录”中以供参考可也。
新版《曹植集校注》,由中华书局重加编校出版,有裨学界良深!绝不宜以此小眚而淹全书之大德,况且这也是尊重作者著述原貌的结果。怎么更好地处理?近读明张燮编《七十二家集》本《陈思王集》,正文卷四中也收录了该诗,但在篇题下有行小注,云:“《世说新语》曰: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张燮显然清楚此诗的真伪性问题,附加此条小注以交代来源。《校注》也不妨照此方式,以编者按在篇题下附加此小注。尽管《七步诗》出自《世说新语》属常识,但如此处理可于“无声”之中避免歧解。新版《校注》是好的开端,期待有更多的六朝别集校笺整理大著付梓问世,从而将六朝文学文献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