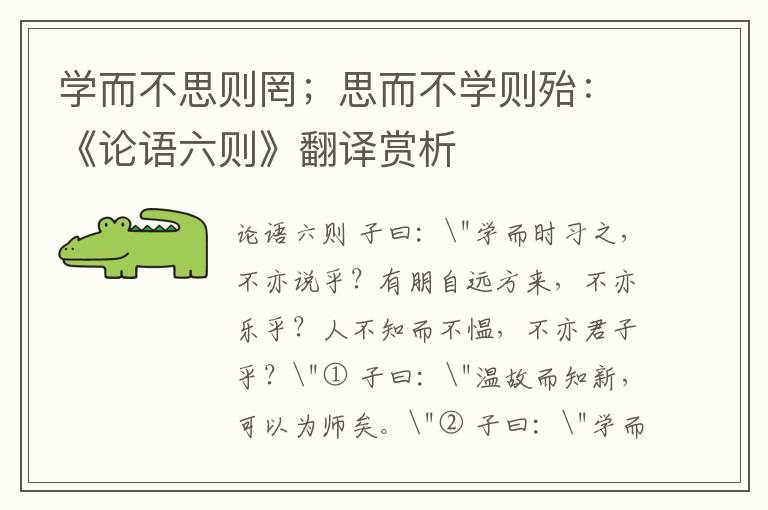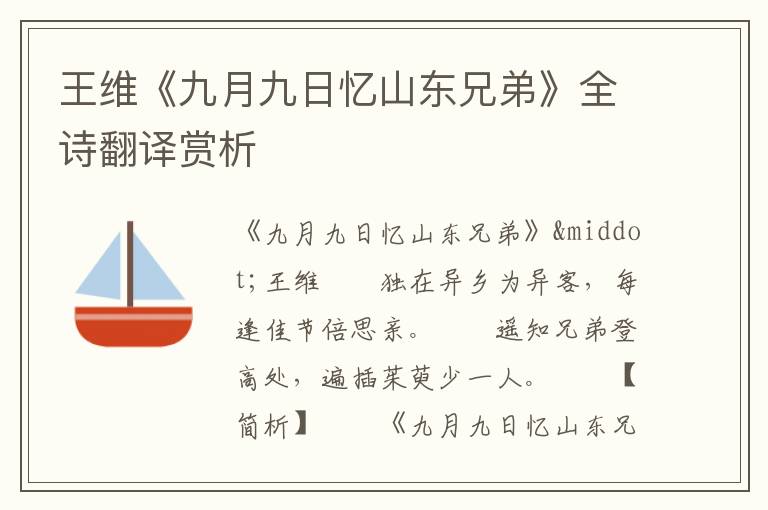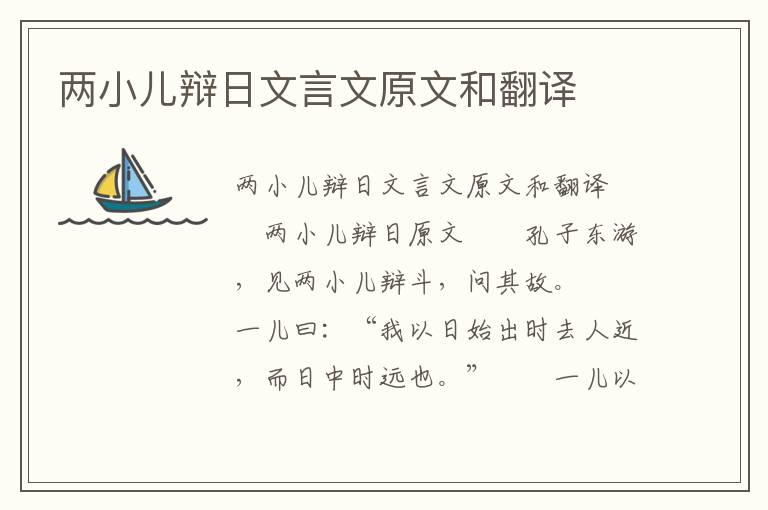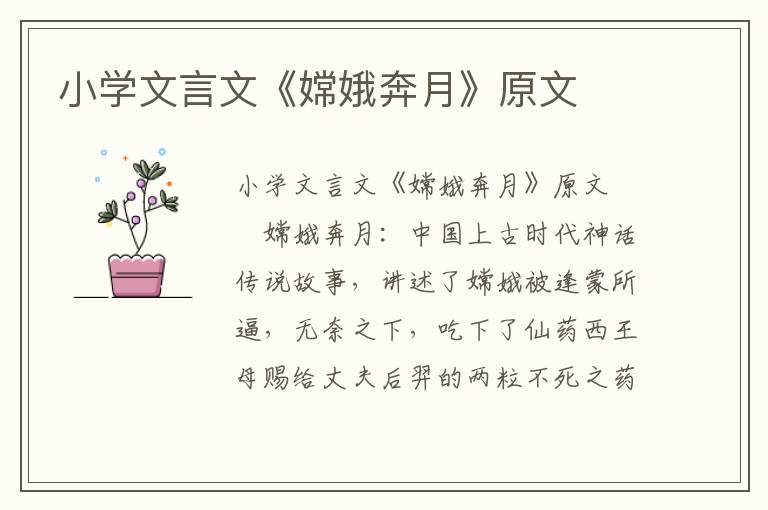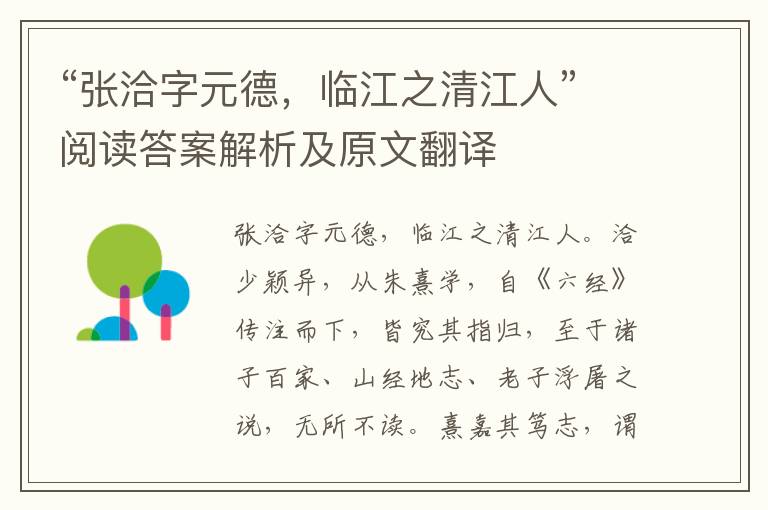【简介】感谢网友“雕龙文库”参与投稿,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方便大家学习。
唐宋诗艺术特征比较研究
唐宋诗之争为中国诗史上聚讼纷繁的一大公案,在历代的唐宋诗之争中,实已包含有对唐宋诗艺术特征的认识。如严羽《沧浪诗话》讲的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向来被认为是对宋诗创作特色的概括,人们对宋诗特征的认识,常通过唐、宋诗的比较来加以说明。在现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中,也一直存在着唐、宋诗之高下优劣的争论,涉及唐、宋诗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的比较。当同光体之类的旧诗成为遗迹,宗唐与宗宋的门户之见不复存在之后,这依然是唐宋诗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1922年为纪念《申报》创刊五十周年而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说:“这五十年(指1872—1922)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他认为,“这个时代之中,大多数的诗人都属于‘宋诗运动’。宋诗的特别性质,不在用典,不在做拗句,乃在做诗如说话。北宋的大诗人还不能完全脱离杨亿一派的恶习气;黄庭坚一派虽然也有好诗,但他们喜欢掉书袋,往往有极恶劣的古典诗(如云‘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南宋的大家——杨、陆、范——方才完全脱离这种恶习气,方才贯彻这个‘做诗如说话’的趋势。但后来所谓‘江西诗’派,不肯承接这个正当的趋势(范、陆、杨、尤都从江西诗派的曾几出来),却去模仿那变化未完成的黄庭坚,所以走错了路,跑不出来了。”很显然,胡适是从提倡白话文学的角度评判宋诗的,肯定宋诗中那些很近白话的诗,而对江西诗派掉书袋的古典诗则持否定态度。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平民文学,要打倒贵族的古典文学,所以当时的桐城派之文和宋诗运动中的江西派之诗,均在被排斥之列。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所谓‘江西派’者,山谷之偶像也。”他将江西诗派归入“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而加以否定。鲁迅在《致杨霁云》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尚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这些新文学运动倡导者的言论,虽非专为研究宋诗而发,影响却十分深远,给宋诗运动以致命的一击,造成很长一段时间唐诗研究受重视而宋诗遭贬斥的局面。
与唐人作诗多出于自然感兴不同,宋诗多讲究命意曲折和修辞功夫。胡云翼《宋诗研究》认为,宋代诗人在创造方面虽没有唐代诗人伟大,但在诗的描写技巧方面有进步。“第一:宋诗格外的整练有规矩,没有唐人不工稳的毛病了;第二:宋诗的描写越发细致,没有唐人粗率的毛病了;第三:宋诗的描写特别冲淡,没有唐人一味豪迈意气的毛病了。”他说宋诗的特色还在于造了一个新诗境,那就是宋诗里面有一种充满了画意的诗异常发达。尽管胡云翼对宋诗特色的把握有可商榷之处,但他从“技巧”与“诗境”两个方面来分析宋诗特色的方式值得肯定。程千帆在1940年写的《读〈宋诗精华录〉》中认为,“唐人之诗,主情者也,情亦莫深于唐。及五季之卑弱,而宋诗以出。宋人之诗,主意者也,意亦莫高于宋。后有作者,文质迭用,固罔能自外焉。”他说:“唐人以情替汉、魏之骨,宋人以意夺唐人之情,势也。浸假而以议论入诗。夫议论则不免于委曲,委曲则不免于冗长,长则非律绝所任,此所以逮宋而古诗愈夥也。其极至句读不葺,而文采之妙无征;节奏不均,而声调之美遂閟。此宋人之短,非宋人之长。”以缘情与主意作为于创作上分别唐、宋诗的主要特征。
唐人作诗尚天人相半,在有意无意之间,宋人则纯出于有意,欲以人力巧夺天工,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缪钺在《论宋诗》一文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漳寻幽,情境冷峭。唐诗之弊为肤廓平滑,宋诗之弊为生涩枯淡。虽唐诗之中,亦有下开宋诗派者,宋诗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论其大较,固如此矣。”他认为宋诗的内容较唐诗更为广阔,能略唐人之所详,而详唐人之所略,虽尽事理之精微,而乏兴象之华妙。宋人作诗讲究熔铸群言,强调无一字无来处,因“凡有来历之字,一则此字曾经古人选用,几最适于表达某种情思,譬之已提炼之铁,自较生铁为精。二则除此字本身之意义外,尚可思及其出处词句之意义,多一层联想。运化古人诗句之意,其理亦同。一则曾经提炼,其意较精;二则多一层联想,含蕴丰富。”他以为唐人律诗,其对偶已较六朝为工,宋诗于此,尤为精细。大抵宋诗对偶所贵在工切、匀称、自然、意远。唐人为诗虽也重句法,而宋诗造句之法,在求生新,求深远,求曲折,以矫俗熟卑近和陈腐。宋人于唐诗用韵之变化处特加注意,喜押强韵,喜步韵,因难见巧,反可拨弃陈言,独创新意。唐诗声调,以高亮谐和为美,而黄庭坚的山谷体诗别创一种兀傲奇崛之响。与唐人作诗相比,宋人从运思造境到炼句琢字和韵调音节,皆有自己的特点,其长处为用意深折,意味隽永,其流弊为喜用偏锋,乏雍容浑厚之美。或专求奇字缀葺成诗,乍观有致而久诵乏味;或求工太过失于尖巧,剥落色相而流于枯淡。
在《谈艺录》中,钱钟书开篇即谈“诗分唐宋”的问题,认为:“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此说一反前人论诗时以朝代区别唐宋的做法,将唐诗和宋诗作为古典诗歌的两种基本体格和审美范式:一以“丰神情韵擅长”,一以“筋骨思理见胜”,前者真朴出自然,后者则刻露见心思。之所以如此,深层的原因是人的性分之殊,钱钟书说:“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唐以前之汉、魏、六朝,虽浑而未划,蕴而不发,亦未尝不可以此例之。”也就是说,并非宋朝人写的诗才叫宋诗,唐朝人写的诗才叫唐诗,这是就时代而言,具体到作家本人,“且又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换言之,一个诗人可能既写唐诗又写宋诗,关键在于其一生的性情变化使之然。
钱钟书《宋诗选注序》认为:“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又说:“凭藉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他认为宋人的习气是“资书以为诗”,所以“把末流当作本源的风气仿佛是宋代诗人里的流行感冒。嫌孟浩然‘无材料’的苏轼有这种倾向,把‘古人好对偶用尽’的陆游更有这种倾向;不但西昆体害这个毛病,江西派也害这个毛病,而且反对江西派的‘四灵’竟传染着同样的毛病。”他认为宋诗的艺术成就虽不及唐诗,但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的宋诗研究几近于空白,而海外却有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宋诗概说》出版。他以为宋诗的重要特征和价值,不仅在于对前代的继承和总结,更重要的在于对传统诗歌意绪表现范围的解放:一是视界的开阔,一是悲哀的扬弃。这也是宋诗区别于传统诗歌的内涵和特征,宋人不但把诗视为抒情或流露感情的场所,同时也把诗当作传达理智的地方,由此形成了宋诗表现的叙述性和思辨性的特征,造成唐宋诗内在的本质区别。他说:“正因为如此,唐诗显得如火如荼,紧凑而激烈。简言之,在匆匆趋向死亡的人生过程中,诗人作诗只能抓住贵重的瞬间,加以凝视而注入感情,使感情凝聚、喷出、爆发。诗人所凝视的只是对象的顶点。这是唐诗之所以显得激烈的原因。唐诗是凝缩而简洁的,但视界的幅度却也因而受到了限制。宋诗则不然。宋人以人生为长久的延续,而且对这长久的人生具有多方面的兴趣,具有广阔的视界。诗人的眼睛不只盯住在产生诗的瞬间,也不只凝视着对象的顶点。他们的视线广泛地环望四周,因此显得冷静而从容不迫。”所以宋诗中不仅悲哀题材的作品很少,即使表现悲哀,也能够客观、冷静地对待,在理性的逻辑之中,仍能透露出希望之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国内有关宋人是否一反唐人规律而不懂形象思维的争论,促使人们对唐宋诗各自的艺术特色进行反思。如陈祥耀在《宋诗的发展与陈与义诗》中指出:历史上有关唐宋诗短长的争论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宋诗不如唐诗,一派认为宋诗较唐诗是有所发展的。这两派都看到了宋诗的一个方面,拘之则偏,合之则全。他说:“宋诗议论多,用典多,散文化的倾向较突出,含蓄抒情和形象思维确有不及唐诗的地方;但它在技巧上力求翻新,力破余地,对唐诗来说,也确有新的发展。”他从比较的角度谈宋诗特征,说:“大抵唐诗善摅情,以韵味胜,宋诗工言理,以意趣胜。唐诗较浑厚,宋诗工委曲。唐诗以气魄雄伟胜,宋诗以态度闲远胜。唐人豪迈者,宋人欲变之以幽峭;唐人粗疏者,宋人欲加之以工致;唐人流利者,宋人欲出之以生涩;唐人平易者,宋人欲矫之以艰辛;唐人藻丽者,宋人欲还之以朴淡;唐人白描者,宋人欲益之以书卷;唐人酣畅者,宋人欲抑之以婉约;唐人多炼实字,宋人兼炼虚字。宋诗文理察密,技巧精细,有逾于唐;而气韵之涵蕴不逮焉。”关于宋诗特征的概括,当时较为流行的还是严羽说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人们认为这虽是对宋诗的批评,可也道出了宋诗的特点,所以常从这几方面来探讨宋诗特征。
在《宋代诗歌的艺术特点和教训》一文中,王水照参照严羽的说法,认为宋诗的三大特点是:散文化、议论化、以才学为诗。匡扶在《宋诗的评价及其特色浅谈》中指出:宋诗除了散文化、多议论之外,语言的通俗化也是主要特色之一。他认为,在宋代“诗人们肯于吸取、提炼民间口语,来丰富和翻新自己诗的语言,造成一种清新流畅、朴实自然的风格。”许多宋诗写得明白如话。通常,人们将严羽讲的“以文字为诗”,理解为“以文为诗”,即诗歌创作的散文化,指把散文的一些手法、章法、句法和字法引入诗中。但胡明在《“以文为诗”和“以文字为诗”》中认为:宋人所谓“以文为诗”,主要是指叙事和言理——尤其是言理——入诗而说的,而其形式特征即结构手段、叙述方法的散文化倾向是次要的内涵。再则,严羽的“以文字为诗”,主要指的是宋代诗风的两个不良倾向:一是雕琢文字,游戏音韵;一是“点铁成金”,挦扯缀补。所以将“以文字为诗”理解为“以文为诗”是错误的,并且,“以文为诗”也不等于散文化。胡念贻在《关于宋诗的成就和特色》中指出:宋诗的数量超过《全唐诗》两倍以上,其中确有大量的好诗,不能用严羽讲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来概括宋朝一代的诗歌。因为这导致人们对宋诗产生两个看法:一是宋诗缺乏生活;二是宋诗缺乏形象。
把严羽对宋诗的批评看作是对宋诗特质的概括,以此为依据论述宋诗,自然会导致对整个宋诗评价的偏低,或者说是把宋诗的缺点当作特点。那么,如何就宋诗在文学史上所取得的成就来探讨宋诗特色,如何就宋诗的具体评价概括总结宋人的艺术个性,就是宋诗研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人们从诗歌意象、文化蕴涵、艺术风韵、题材范围、创作追求和审美理想等诸多方面,对唐、宋诗的艺术特征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可贵探索,形成了以下一些看法:
唐诗创作以自然意象为主,宋诗多为人文意象。宋代作家的人文修养较唐代作家要高出许多,故人文意象在宋诗中亦提升到了突出的位置,反映一代宋人的读书情趣和书生本色。霍松林、邓小军在《论宋诗》中指出:宋诗的特质是发挥人文优势,即通过人文意象的描写与典故、议论的运用,表现富于人文修养的情感思想,体现一种有品节又有涵养的精神。“宋诗用典之多超过了唐诗,这固然与宋人读书多有关,但更与宋人的人文情趣息息相关。用典的妙处,在于增添诗歌语言的渊雅风味。”用典除了是一项古为今用的语言艺术手段,也是人文意象的渊薮。宋诗的用典,一是借以深化所要表达的情感思想,二是借以寄托尚友古人的人文情怀。宋诗的议论也发自人文修养,是抒情的延伸和深化。“自然意象的淡化,人文优势的提升,规范了宋诗淡朴无华的基本风貌。崇尚品节的精神,艺术上的刻意求新,决定了宋诗瘦硬通神的风格要素。富于人文修养的情致,则产生了宋诗渊雅不俗的独家风味。”与唐诗的兴象玲珑不同,宋诗之美是一种风致美,而风致是人文情趣的体现,是品节涵养的呈露。
唐、宋诗是不同类型文化的产物,宋诗的文化蕴涵和艺术风韵有异于唐。宋文化发轫于中唐、复兴于庆历、而具形于元祐,宋诗的发展亦然。龚鹏程在《江西诗社宗派研究》中指出:宋文化形成后,乃有所谓宋诗,有宋诗,方有唐宋诗之争,“所谓唐,所谓宋,非朝代之别,乃不同风格类型之分,犹文化类型中可区为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也。”他认为自中唐哲学突破后,宋诗之风格特质方逐渐形成,表现于体制变迁、反省之创造和道器合一等方面。宋人的创作形态,非表现之创造,而为反省之创造,创作方式趋于以复古为开新一路。又宋人通艺事于妙道,论书画论诗歌,以人格比合风格,几与论修身同义,“方是时也,艺术制作,既与人格修持无异,评诗论人,亦当具同一眼目。”刘乃昌、王少华的《宋诗论略》认为,与唐代士人相比,宋代士人更重品节,宋人学陶多着眼于陶诗的远韵清操、高情逸趣,宋人学杜的作品也大都体现出一种人格美;宋诗较少唐诗那种浑雅醇厚的韵致,而多含睿智哲思,长于在写景抒怀中寄寓诗人对于历史、社会、人生、政治等问题的种种见解,以理取胜,又不抽象说理,对人生体验更加深化,达到了哲学的高度;超越唐人重音容声色渲染的艺术表现定势及窠臼,宋诗的特色在于看似朴淡而意蕴深隽,归于平淡简古,进入高风绝尘的雅趣清境;与唐人作诗注重声调格律的响亮圆润不同,宋人发展了拗句和拗律的体制,从而形成了宋诗的苍劲风骨。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高峰,宋诗的价值不在于类似唐诗,亦不必与唐诗争高下,而在于能在艺术风格和题材内容方面开拓出新。在《宋诗之传承与开拓》一书中,张高评专就宋人咏史、咏物等题材的翻案诗、宋代的禽言诗,以及宋人咏画、题画诗所创格的“诗中有画”之表现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以说明“宋诗既有传承古学之襟抱,又富于开拓之气象,故能于唐诗登峰造极之后,别开生面,蔚为与唐诗争驰抗衡,风格独具之自家特色。”认为宋诗或发扬光大唐诗之优长,凡唐人浅言少言泛言者,宋人深言多言切言之,必期至于淋漓酣畅而后已;或喜作理性思考,深造有得,创作家与理论家纷纷作“出位之思”,于是而有诗画一律、诗禅相融、以文为诗、以诗为词、诗书画相济诸事实与理论。朱刚的《从类编诗集看宋诗题材》,就宋人按题材类编的两种集子进行统计,指出宋诗取材广、命意新的特点的形成,在于“缘情”和“体物”的界线消失,取材上不受限制,使诗歌题材扩大至于“无所不包”的境地。在政治和社会问题题材的诗歌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诗歌成为士人风雅生活的必备内容,生活中随处而有的诗意都被发掘出来,诗不但是千古事业,而且就是生活。故诗无所不在,诗的题材无所不包。
与唐诗的情来、气来、神来而声色并茂不同,宋人论诗谈艺常言“脱俗”,强调艺事的精深华妙和风格的超迈流俗,这最终取决于作家的人文道德修养,是一种与诗人的人品、人格紧密相联的精神境界。秦寰明在《宋诗的复雅崇格倾向》中指出:宋代诗歌创作中存在着复雅崇格的倾向。由复雅而归于崇格,反映出宋人注重创作主体内在的超越流俗的人格精神和高逸情趣,进而致力于诗歌的平淡境界和思理筋骨的逻辑力量的追求。因崇格较之复雅更须求诸作者的胸襟气骨,并且具体而微地体现于用笔的技法力度,这是对唐诗主情传统的反拨和超越。张毅认为:作为宋诗代表的苏、黄诗学,虽讲求理智之沉思,亦重情气之灌注,追求的是自然之理和人生哲理融为一体的理趣,其最终所要达到的是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老境美,一种外枯而中膏、似癯而实腴的成熟之美。宋人对老境美的追求,体现为襟怀淡泊、思致细密和情意深邃等方面。宋人把“平淡”作为作家艺术成熟的标志,注重化巧为拙、藏深于朴,用自然素朴的表现形式反映出蕴意深远的人生感悟。宋诗拔去浮言腴语的瘦硬风格,是宋人“造平淡”的一种特殊方式,以命意深折和词理的细密为特征,讲究语意老重和规模宏远。就更深一层次的情感表达而言,老境美所反映的是一种人世沧桑的凄凉和强歌无欢的沉郁,它源于当时作家心理感情中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属于一种带有理性批判否定精神的情感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