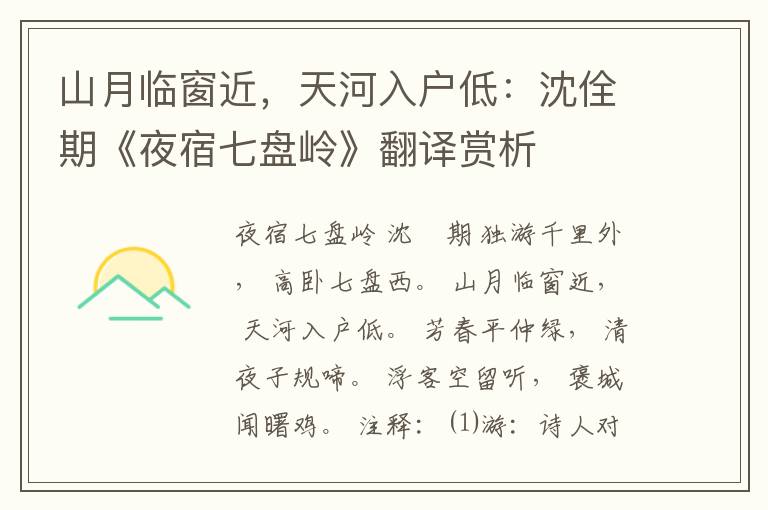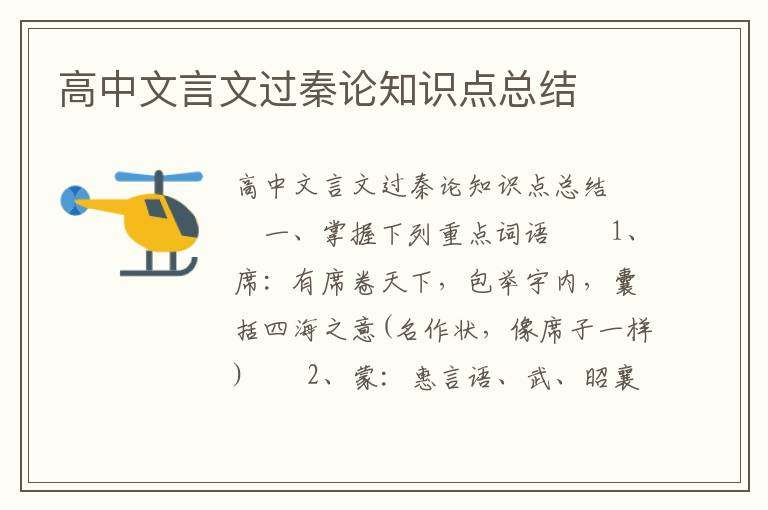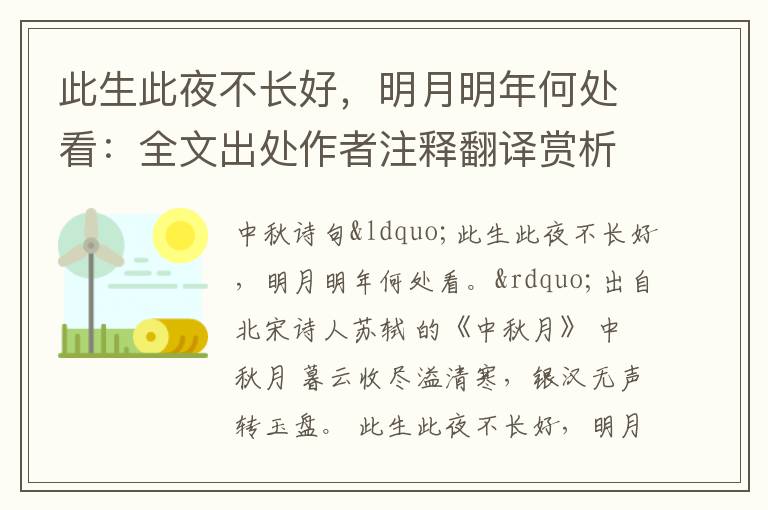【简介】感谢网友“雕龙文库”参与投稿,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方便大家学习。
作者: 东方朔
【原文】:
客难(nàn)东方朔曰:“苏秦、张仪壹当万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shēng)记,著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可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
“是故非子之所能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擒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则强,失士则亡,故说(shuì)得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廪(lǐn)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与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shuí),并进辐凑者不可胜(shēng)数。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传曰:‘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事异。
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yòu)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学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鹡鸰(jí líng),飞且鸣矣。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诗》云:‘礼义之不愆(qìan),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liú),所以蔽明;纩(tóu kuàng)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kuí)而度(duó)之,使自索之。’盖圣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
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块然无徒,廓然独居,上观许由,下察接舆,计同范蠡(lǐ),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予哉?若夫燕之用乐毅,秦之任李斯,郦食其(lì yìj ī)之下齐,说(shuí)行如流,曲从如环;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国家安:是遇其时者也。子又何怪之邪?
语曰:‘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tíng)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由是观之,譬由鼱鼩(jīng qú)之袭狗,孤豚(tún)之咋(zé)虎,至则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处士,虽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
【译文】:
客人诘问东方朔道:“苏秦、张仪一逢万乘之国的君主,就身居卿相的地位,恩泽留到后世。现在大夫您学习先王的学说,喜好圣人的道理,熟读《诗》《书》和诸子百家的文章,记不清有多少,著书立说见于竹帛,磨破嘴唇、磨掉牙齿,全都记在心里永不忘记。您喜好学问乐守圣人之道的功夫,是非常清楚的。自以为才能天下无双,可以算是知识渊博才智出众了。可是竭力尽忠,来侍奉皇帝,空废时光持续长久,累积数十年,官位只不过是个执戟的侍从官罢了。想来您可能在行为上还有什么过失吧?兄弟姊妹,都无处容身,这是什么缘故呢?”
东方先生长叹了一口气,抬头回答他说:
“这种原因不是您所能全部了解的。那时是一个时代,现在又是一个时代,怎么能同等看待呢?那苏秦、张仪的时代,周王朝崩溃,诸侯不朝贡,都尽力征战,争权夺利,互相攻伐,以至兼并成为十二个国家,不分胜负,谁得到士就会强大,谁失去士就会败亡,因此游说能够流行。于是他们得以身居高位,内则珍宝充足,外则仓库盈满,恩泽留传到后世,子孙可以长期受用。现在却不是那样,圣上恩德流布,天下畏惧,诸侯服从,国内同海外如衣带相连,比倒扣着的小盆还要安稳。天下到处一样,全国合为一家,举办事情,就像在手掌上摆弄东西一样容易,有才能和无才能又有什么区别呢?遵循着自然之势,人们无不各得其所。被抚爱就安宁,被驱使就劳苦,被重视就为将军,被轻视就成俘虏,被提拔就可到青云之上,被压抑就可到深渊之下;用时就像得势的老虎,不用时犹如潜藏的老鼠。即使想要尽力保持节操,献出忠心,哪里知道怎样去作呢?天地那样广大,士民那样众多,竭尽精力去游说,聚集并进的数也数不清。全力想得到天子的恩宠,结果却是有的困于衣食,有的找不到门路。假使苏秦、张仪和我生活在当今这同一时代,可能连一个管理档案一类小差事也得不到,哪里还敢想到当侍郎呢?古书上说:‘当天下没有灾祸的时候,即使圣人,也无法施展他的才能;当朝廷上下和睦相处的时候,即使贤才,也没有办法建功立业。’所以说,时势不同事情也就不会一样。
“尽管如此,我又怎么可以因此而不努力加强自身的修养呢?《诗经》上说:‘在室中撞钟,声音传到室外’,‘仙鹤在水边长鸣,声音上闻于天’,如果能够加强自身修养,又何愁不能显荣呢?姜太公亲身以仁义行事,七十二岁时,才得到周文王、武王的重用,施展了他的谋略,最后被封于齐,后世七百多年不曾断绝。这就是士日夜孳孳不倦、努力学习勤勉修身而不敢懈怠的原因。就如同鹊鸰鸟一样,一面飞行一面鸣叫。古书上说:‘天不因为人厌恶寒冷而去掉冬季,地不因为人厌恶险阻而去掉广阔,君子不因为小人大吵大闹而改变德行。天有正常的规律,地有正常的形状,君子有正常的德行。君子正道而行,小人则只考虑得失。《诗经》上说:‘按礼义行事没有差错,何必担心别人的闲话。’‘水过于清彻就没有游鱼,人过于明察就没有伴侣。礼帽前面垂旒,是用来遮蔽视线;两旁悬黄绵,是为了堵住耳朵。’眼睛应该有所不见,耳朵应该有所不听。要用大的长处,要放过小的错误,就是对一个人不求全责备的意思。‘弯曲的要让他直过来,使他自有所得,要优柔宽和地对待他,要揣情度理地诱导他,让他自己探索追求它。’圣人的教化就是这样,要让他自有所得,自有所得,就敏捷而且广大了。
“现在的没有出仕的人,虽然不为当时所用,孤独无伴,空虚独处,但是上学许由,下效接舆,智同范蠡,忠合子胥,在天下和平之时,按道义行事。没有相合的人,本来是应该的。您何必怀疑我呢?至于乐毅被燕王重用为将军,李斯被秦王任用为丞相,郦食其用言辞取得齐七十余城,他们游说进言,像水流那样顺利,人主听从他们的话,就像圆环一样转动;他们所想的一定能够得到,他们的功绩就像山一样高;他们使海内得以平定,国家得以安宁:这些人之所以得志,都是由于他们遇到了好的时机呀。您又何必感到奇怪呢?
“常言道,‘用竹管看天,用葫芦瓢量海,用竹枝撞钟,怎么能够弄清星辰的分布,测出大海的浩瀚,考究出钟声的宏亮呢?’由此看来,譬如让小鼠去攻击狗,让小猪去咬老虎,一去就会没命,有什么用处呢?现在以最愚笨的人来非议不出仕的人,即使想要不受到困窘,也一定办不到。这正好足以表明他不知道变通而终于不明白大道理啊。”
【评介】:
本文选自南北朝梁萧统《昭明文选》,李善注说:“汉书曰,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推(指)意放荡,终不见用,因著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这表明东方朔这篇文章是因为不被重用,“位卑”不得志,因而借客之洁难,用托辞自解的方式,来发发牢骚而已。
文章分诘难和答辞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假设客人诘难自己的方式,提出问题:你既然好学乐道,博闻辩智,为什么却长久不得重用呢?开门见山,就把文章的中心问题摆出来了。第二部分是答辞,则由自己做出了全面的回答。
在回答中,首先分析诘难中所提到的苏秦、张仪所生活的时代和当今时代的不同,指出时异则事异,不能以古衡今,从而说明为什么苏秦、张仪之说得行,而自己却“无所施才”、“无所立功”的原因。接着,从正面表达情志,表示自己虽不得志于现时,但却要保持自己的人格,不可以“不务修身”,而要“修学敏行”,按正道而行,做到自有所得。接着再次用乐毅、李斯、郦食其的“说行如流”,“功若丘山”来说明并非自己无才,只是不遇其时而已。最后指出客人诘难所见者小,不知通变,不懂得大道理,以此总括作为答辞的结束。文中分析苏、张与自己时代的不同,写出乐毅、李斯等各自有不同的机遇,两两相对,形成了鲜明对比;表达志向时引传、引诗,引经据典,既有理有据,又堂堂正正,从而显出了自己的人格;“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撞钟”,“鼱鼩之袭狗,孤豚之咋虎”,连用一连串比喻来说明诘难的见识短浅,调侃中自有风趣。
文章表面看来,似乎是东方朔在自我安慰、自我宽解。你看,他明明说,生活在当今的时代,“虽有圣人,无所施才”,“虽有贤者,无所立功”,那是很自然的;那乐毅、李斯、郦食其之所以“说行如流”,建立功业,只是“遇其时”而已;至于自己,则要“务修身”,“道其常”,自得其乐。表现得多么坦然,多么豁达呀!而实际呢,却并非如此,话里面还有话,文章背后还有文章。他说现今和苏、张时代不同,连圣人、贤者也无法“施才”、“立功”,正表明当今的时代压抑了人才;他说乐毅、李斯等人“遇其时”,正表明自己的不遇时;他说自己要“道其常”,“自得之”,正是在貌似豁达中表现自己内心郁积着不得志的满腔愤懑;他用诙谐来发泄牢骚,只是表面故作旷达而已。甚至表面所否定的客人诘难的问题,正是文章背后所要肯定的东西。他一方面反话正说,故意设为客问。假为正面驳斥,滑稽风趣,使文章显出幽默诙谐的喜剧特色,但是,在滑稽幽默背后,却深藏着一颗痛苦的心,在喜剧的后面是悲剧。它抒发了作者久沉下位、怀才不遇的抑郁悲愤之情;同时,另一方面也揭露了社会和当政者对人才的压抑。当然,这对整个封建社会来说,是有普遍意义的。
这篇作品本是一篇散文,全篇通过客人诘难,主人作答的论辩方式阐明观点、抒写感情。有问有答,形似论辩谈话的记录,实则有论有议,有感情的抒发,达到了一般议论文章难以做到的畅所欲言而又尽情发泄的目的,是一篇发议论抒感慨的妙文。文中以散为主、骈散相间,句式间有排偶用韵,再加上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因此虽属散文,却具有赋的某些特色,因而开创出了一种特殊的文体形式,后人起而模拟,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韩愈《进学解》,就是这种形式的继承和发展。对这种形式,萧统在《文选》中为之单列一类,称之为“设论”,后人把它归并到赋里,认为是赋体的一种特殊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