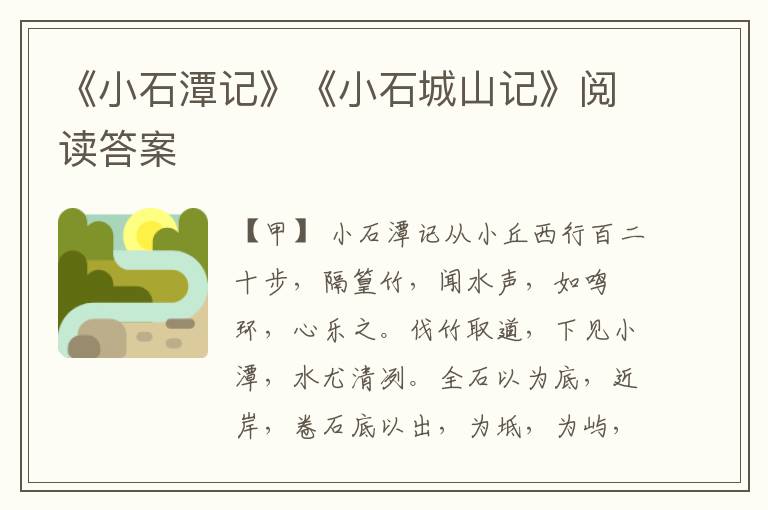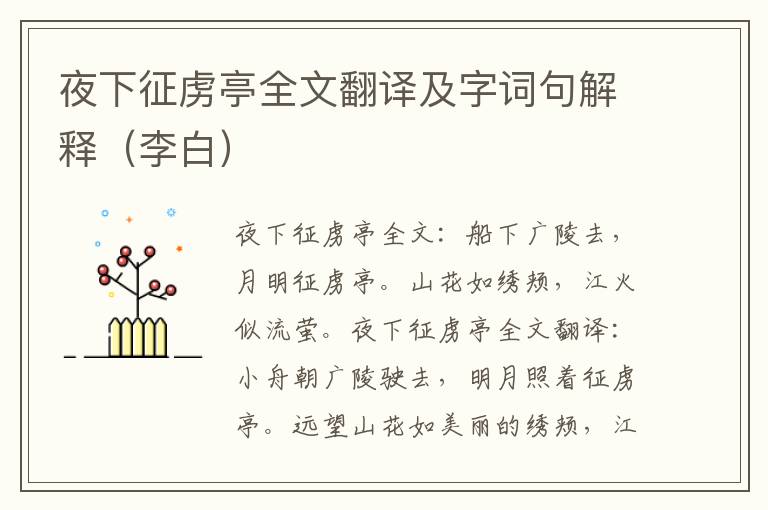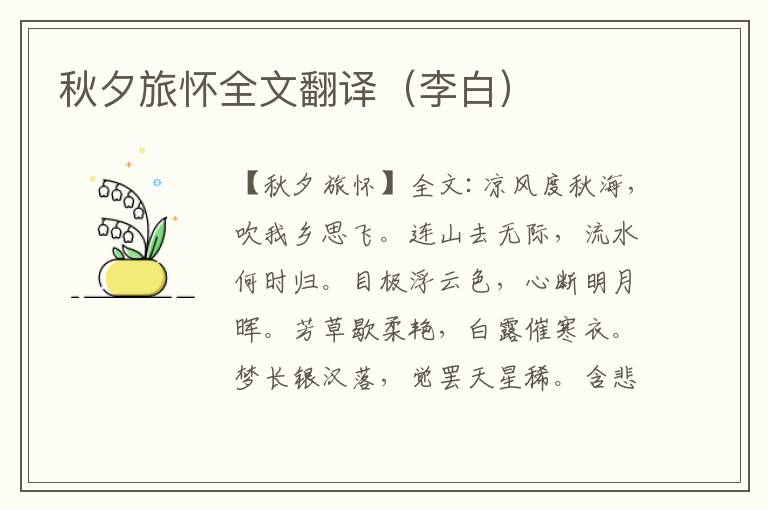【简介】感谢网友“雕龙文库”参与投稿,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方便大家学习。
古风其八全文:
咸阳二三月。
宫柳黄金枝。
绿帻谁家子。
卖珠轻薄儿。
日暮醉酒归。
白马骄且驰。
意气人所仰。
冶游方及时。
子云不晓事。
晚献长杨辞。
赋达身已老。
草玄鬓若丝。
投阁良可叹。
但为此辈嗤。
古风其八全文翻译:
二三月的咸阳城,宫柳发出像黄金一样的嫩枝。
有一个戴着绿头巾的家伙,原本是卖珠子的轻薄少年。
日暮之时,他醉酒而归,骑在白马上,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他冶游所到之处,人们都仰而避之,害怕他的气焰。
扬子云老不晓事,到了晚年还献什么《长杨赋》。
到了皇帝手中时,扬雄已老,满头白发还在写《太玄经》。
他的投阁之举实在令人叹息,只落得个为此辈小儿嘲笑的下场。
古风其八字词句解释:
“绿帻”二句:《汉书·东方朔传》:(汉武)帝姑馆陶公主,号窦太主,堂邑侯陈午尚之。午死,主寡居,近幸董偃。始偃与母以卖珠为事,偃年十三,随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见曰:“吾为母养之。”因留第中,教书计、相马、御射,颇读传记。至年十八而冠,出则执辔,入则侍内,为人温柔爱人。以主故,诸公接之,名称城中,号曰董君。主因推(举荐)令散财交士,令府中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与偃善,谓偃曰:“足下私侍汉主,挟不测之罪,将欲安处乎?何不白主,献长门园,此上所欲也。如是则上知计出于足下,则安枕而卧者,无惨怛之忧。”偃入言之主,主立奏书献之。上大悦,更名窦太主园为长门宫。上以钱千万从主饮。后数日,上临山林,主自执宰(亲自操作)蔽膝,道入,未坐定,上曰:“愿谒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顿首谢。有诏谢,主簪履起,自东厢自引董君。董君绿帻傅鞲(着皮质袖套)随主前,伏殿下。主乃赞(赞礼):“馆陶公主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谒。”因叩头谢,上为之起。有诏赐衣冠上。当是时,董君见尊不名,称为主人翁,饮大欢乐。主乃请赐将军列侯从官金钱杂缯各有数。于是懂君贵宠,天下莫不闻。
“子云”六句:据《汉书·扬雄传》: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孝成帝时,待诏承明之庭,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以风。哀帝是,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依附)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访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又,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收雄,雄从阁上自投下,几死。
古风其八赏析(鉴赏):
诗可以分为两段。“冶游方及时”之前八句为第一段,“子云不晓事”之后六句为第二段。两段诗将社会上身份不同,生活态度不同,境遇也不同的两种人并放在一起,通过他们的反衬映显,表现出诗人对人生和文人命运的思考。
第一段前两句描写春景,点明时节和地点,景色艳丽。三四句用汉朝董偃的故事。“帻”是包发的头巾,当时按人们身份贵贱的不同,头巾的颜色是有区别的,“绿帻”是平民百姓的用物。《汉书·东方朔传》载:董偃少年时随母卖珠,以维持生计。他因此出入武帝姑母馆陶公主家,后得馆陶公主宠幸,与她同居,成为她的情夫。一天,武帝至馆陶公主家饮宴,董偃头戴绿帻谒见,受到武帝的封赏,后来又被武帝宠用。据此,这首诗的第一段乃是针对得势的外戚,讥刺他们骄纵放荡,洋洋自得。诗歌描写:深春的长安,宫院旁边的柳条吐出金黄色的芽颗,秀嫩鲜丽。在这春光媚丽的季节,外戚的“轻薄儿”们更加放肆恣乐,招摇过市。你看:他们不知又在哪里饮酒作乐了一天,直到日暮才醉醺醺地回去。连他们坐下的白马也神气活现,趾高气扬地奔驰在长安道上,更何况它们的主人,其骄横的“意气”实在使人仰慕企羡。他们享有特权,自然要及时寻欢浪玩,否则岂非太傻。“人所仰”三字的作用在于显出“轻薄儿”“意气”骄横之意,“冶游方及时”既是诗人描述“轻薄儿”及时作乐的行为,也是替他们说出处世的态度。李白“凡所著述,言多讽兴”。(李阳冰《草堂集序》)这一段诗自然会使读者产生诗人不仅是刺古也是讽今的联想,它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唐天宝年间杨国忠外戚集团,感受出诗人的厌恶之情。
第二段写扬雄的遭遇。扬雄字子云,西汉著名的辞赋家、哲学家。《长杨赋》是他的辞赋代表作之一,《太玄经》是他的哲学著作。“不晓事”指扬雄书生习气太浓,不熟谙世故吏道。《长杨辞》即《长杨赋》,是扬雄四十多岁时的作品。加“晚献”二字,是为了强调他在仕途上可供利用的机会到来得太晚。后面紧接以“赋达身已老”,意谓扬雄献上《长杨赋》等辞章,然而等他以辞赋扬名,年岁已老。其实扬雄赋名称著,不算甚晚,李白以“老”视之,语气带有夸张。《玄》即《太玄经》。汉哀帝时,董贤等佞臣得势,对趋附者授以高官厚禄,扬雄在家著《太玄经》,泊如自守。“鬓如丝”形容头发斑自。诗人说扬雄苦心精思作赋著书,至老仍不能得志,这已经是相当可哀了。可是更可悲的是,他在晚年又受了一场很大惊吓。《汉书·扬雄传》载:扬雄的学生刘棻被王莽治罪,将株连扬雄。当狱差前来收捕时,扬雄从他校书的天禄阁跳下自杀,几乎摔死,后被赦。扬雄求闻达既已不易,暮年又遭到这一场祸难,这实在令人感慨万端。然而得势的外戚及其“轻薄儿”们,不需要刻苦努力,只凭藉他们特殊的关系和背景,就可以高高在上,作威作福。他们对扬雄又是写什么《长杨赋》、《太玄经》,又是畏祸“投阁”,心里觉得这个书生愚蠢之极,因此扬雄只可供他们嗤笑而已。
前后两段诗,一边写外戚权贵、“轻薄儿”们耀武扬威,花天酒地,一边写文人困顿坎坷,祸随身危,通过他们遭遇的强烈反差,表达了诗人刺世讽时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