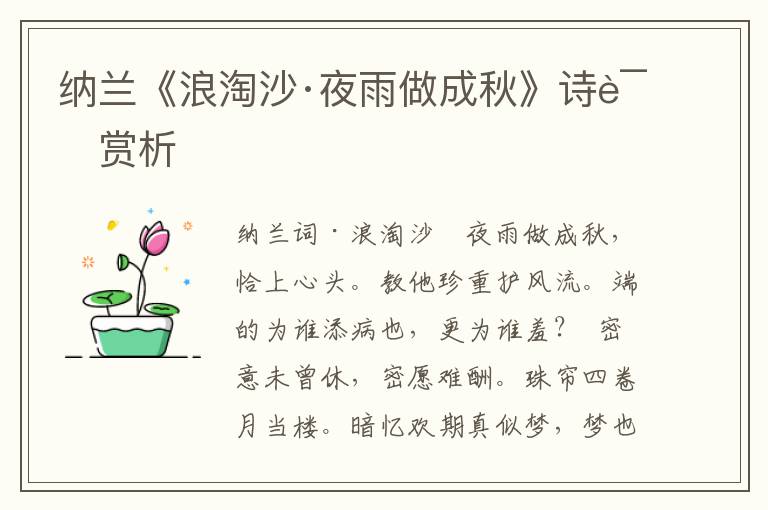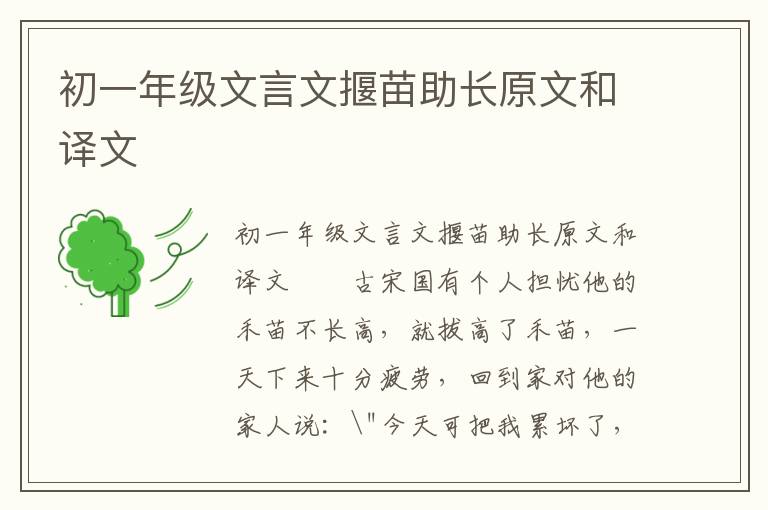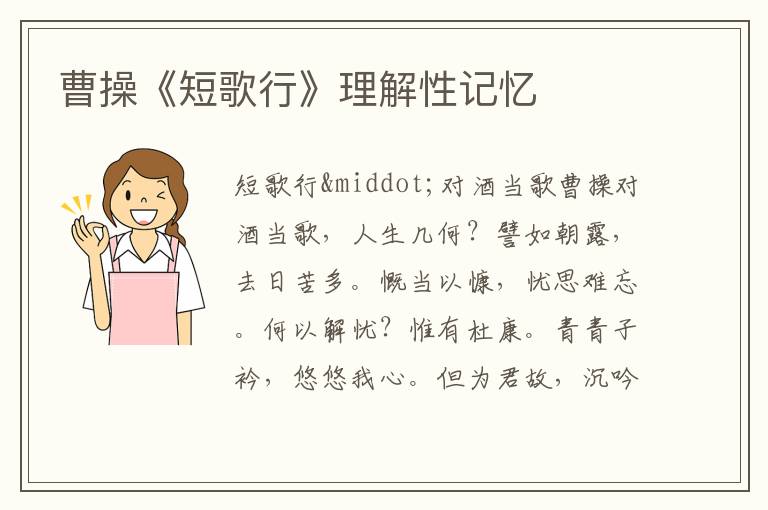【简介】感谢网友“雕龙文库”参与投稿,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方便大家学习。
李白有一首轶诗,一直未收入其诗文集中。清人王琦注《李太白文集》,始据宋人赵令畤《侯鲭录》卷二等的一则记载,将其收入《诗文拾遗》中,名为《题峰顶寺》:“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王琦《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王琦并引用了若干史料,对此诗是否为李白所作存疑。当代几种有影响的李白诗注本基本倾向认为此诗为宋人所作而伪托李白。其根据似乎很简单,那就是:“诗似少年所题,蕲州非李白少年行踪所至。”(参看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版;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郁贤皓主编《李白大辞典》“题峰顶寺”条(作者为陶敏)也认为“李白少年未至蕲州,谓白少年作无据”。 郁氏编著《李太白全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亦未收入此诗。上述几位学者对李白诗的意见有很多分歧,但对这首诗的真伪判断上却惊人的一致。众多学者之所以做出这种推断,主要是因为根据宋代若干史料,这首诗的署名相当复杂,分别有李白、王禹偁、杨亿、晏殊、孟观等说法,真所谓聚讼纷纷,莫衷一是。而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研究李白的学者对宋代涉及这首诗的若干史料,一直皆是平行而观,各说各话,很少仔细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分辨其真伪。有鉴于此,本文试对宋代有关史料作出全面排比分析,以期确定这首诗的原创者,亦对这首诗在宋代的演化过程作出一些新的推断。
一
宋代最早涉及此诗的史料不是《侯鲭录》,而应为王得臣的《麈史》。王得臣的生卒年不详,所知者仅有:
字彦辅,自号凤亭子,安陆人。受学郑獬、胡瑗,嘉祐四年(1059)进士,官至司农少卿,乞病归。所著《麈史》三卷,于当时制度,及考究古迹,极为精核。(《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台湾鼎文书局版)
仅据其为嘉祐四年进士,便可知王得臣的年龄远大于赵令畤,因为赵令畤的生卒年是可以确定的,据有关史料,赵令畤(1061—1134),字德麟,燕王德昭玄孙。元祐中签书颍州公事。坐与苏轼交通,罚金入党籍(《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台湾鼎文书局版)。1061年即嘉祐六年,赵令畤诞生之时,王得臣已中进士两年。从《侯鲭录》的记载看,此书当作于赵令畤晚年,故从时间上推断,《麈史》成书远在《侯鲭录》之前是没有问题的。《麈史》是如何记载此诗发现经过的呢?其全文如下:
南丰曾阜子山尝宰蕲之黄梅,数十里有乌牙山,甚高,而上有僧舍,堂宇宏壮。梁间见小诗,曰李太白也。“夜宿乌牙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布衣李白。”但不知其字太白所书耶?其碑归于丞相吴正宪公,李集中无之,如安陆石岩寺诗亦不载。(王得臣《麈史》卷中,四库全书本)
曾阜何时宰蕲之黄梅,《麈史》没有交代,但南宋刘宰文集中也有一条重要资料,向来无人提及,其文为:
李太白游蕲之黄梅,留诗乌牙山,曰:“夜宿乌牙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句律峥嵘,超越千古。寺僧不异,委之梁间。元丰中,曾阜子山宰是邑,得之,惊喜。顾不能寿之石,使太白书迹与此山俱传,而私以遗当路,过者憾之。(刘宰《漫堂集》卷二十四《书明秀轩米元晖诗后》,四库全书本)
综合王、刘二人的记载,可归纳如下:曾阜于元丰年间任职蕲州,在距离黄梅数十里处的乌牙山,偶然发现了一块题诗碑,全诗为“夜宿乌牙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署名为“布衣李白”。曾阜将此碑取回,送给了当朝丞相吴正宪公即吴充。考《宋史》本传,吴充卒于元丰三年
(1080,见《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吴充传》),则刘宰所谓“元丰中,曾阜子山宰是邑”,应在元丰三年吴充去世之前。这些时地、人物皆是可以确切考知的,毫不模糊,故王得臣、刘宰的记载是相当可靠的。王得臣指出:“其碑归于丞相吴正宪公,李集中无之,如安陆石岩寺诗亦不载。”需要指出的是,王得臣特别关注李白此诗的发现过程,应与其为安陆人,故特别关注其乡土文献有关。这首李白轶诗,确实不载于宋刻本《李太白文集》中。众所周知,第一部宋刻本《李太白文集》正是刊刻于元丰三年。宋敏求增补旧本李白集,得诗近千首,曾阜之兄曾巩为之考定次序。苏州太守晏知止予以校正刊行,为《李太白文集》三十卷,于元丰三年刻于苏州,即所谓“苏本”。无论是曾阜还是王得臣、刘宰,都确信此诗确是为白所作。刘宰甚至认为,李白此诗句律峥嵘,超越千古,本来可以与乌牙山一起名传千古的,但曾阜将此碑“私以遗当路
(即指吴充),过者憾之”。也就是说,这块碑送给吴充,仿佛明珠投暗,导致李白此诗湮没无闻,甚为可惜。当然,从时间上看,元丰三年刊刻的《李太白文集》是不可能将这首诗收入的。后世学者对李白此诗的质疑应该说都源于此。其后,关于这首诗,又出现了种种不同的“版本”。首先为赵令畤的《侯鲭录》卷二:
曾阜为蕲州黄梅令,县有峰顶寺,去城百余里,在乱山群峰间,人迹所不到。阜按田偶至其上,梁间小榜,流尘昏晦,乃李白所題诗也。其字亦豪放可爱,诗云:“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小注:或云:“王元之《少年登楼》诗云: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赵令畤《侯鲭录》,孔凡礼点校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
曾慥所著《类说》中也有两处涉及此诗,分别为卷十五《李太白峰顶寺诗》则:“曾阜为蕲州黄梅县令,有峰顶寺,去城百余里,在乱山中,人迹不到。阜按田偶至梁间小榜,流尘昏晦,乃李白所题诗也。诗云:‘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卷五十七《峰顶寺诗》则又谓:“蕲州黄梅县峰顶寺,在水中央,环伏万山。曾阜为令,因事至其上,见梁间一榜,尘暗粉落,涤拂读之,乃太白诗也:‘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世传杨文公幼时诗者误。”亦改首句“乌牙寺”为“峰顶寺”,从内容看,其史料来源应为赵令畤。
表面上看,赵令畤、曾慥的记载与王得臣、刘宰的记载相差不多,但细微处实有很大差异。首先,“县有峰顶寺,去城百余里”的说法不确。《景德传灯录》卷二十有“蕲州乌牙山彦宾禅师”(《大正藏》第五十一册),从其辈分看,此僧当为中晚唐时人。南宋王象之作《舆地纪胜》卷四十七“蕲州·乌牙山”条,也引王得臣之说,明确此诗为李白所作,并谓:“南乌牙山有灵峰院,在黄梅县东北五十里,有白居易所撰碑”(王象之《舆地纪胜》,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云云,可证王得臣“数十里有乌牙山”之说确切,而赵令畤“去城百余里”的记述模糊不确。其二,王、刘之文皆未言李白诗碑的书法情形,也就是说,他们只记得诗的内容,至于碑,可能并未亲见或质疑其为李白亲书,故不言。王得臣谓:“不知其字太白所书耶?”可见其审慎态度。但他相信,即使字不是李白所书,但诗应是李白所作。这也从侧面证明,他对于这首诗是经过一番研究的,故所记反而不误。但赵令畤的记载则多了一句“其字亦豪放可爱”,仿佛曾亲眼看到过此碑,但所记李白诗与王、刘二人所记字句有异。其三,赵文后有一小注:“或曰,王元之《少年登楼》诗云云”,这是此诗首次出现不同作者的说法,王元之即王禹偁。笔者认为,后人多有将李白题诗与宋人模拟之作混同者,当代学者断定李白此诗为伪作,譬如认为这首诗必是“少年之作”等,也是顺着赵令畤的这则材料而来的。比较起来,王得臣、刘宰的记载当更为确切。钱钟书先生《宋诗纪事补正》对这几位作者的诗也做过一些考订,认为“属名之争,注家纷争不已,姑两存之为妥”(参看王水照《钱钟书先生与宋诗研究》,《文汇报》2002年第0406期)
其后,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又提出一个新的说法:
世传杨文公方离襁褓,犹未能言,一日,家人携以登楼,忽自语如成人,因戏问之:“今日上楼,汝能作诗乎?”即应声曰:“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怕惊天上人。”旧见《古今诗话》载此一事。后又见一石刻,乃李太白夜宿山寺所题,字画清劲而大,且云“布衣李白”作,岂好事者窃太白之诗以神文公之事欤?仰亦太白之碑为伪耶?(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0年版)
谓杨亿幼年一直不说话,一日忽然能言,且出口成章,吟出一首诗,使得此诗作者更加扑朔迷离。但周紫芝提出两点可能:或者是有人“窃太白之诗以神文公之事”,或者是“太白之碑为伪”,他自己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判断。其实,一个刚会说话的幼儿,张口便吟出“危楼高百尺”这样的诗来,“神其迹”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周紫芝虽未明言,但他的态度应是可以推断的。他也说曾见过一石刻,“字画清劲而大”,上面有题为“布衣李白”作的一首诗,显然正是指曾阜发现的那块碑。南宋孙奕的《履斋示儿编》卷九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
李白《题峰顶寺》云:“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乃知晏元献《危楼》诗全似之。(孙奕《履斋示儿编》卷九,四库全书本)
这里又说:北宋名相晏殊有一首《危楼》诗,与李白的诗“全似”,虽未具体举出晏诗,但显然与王禹偁、杨亿之事类同。这则材料向来无人重视,但我以为无意中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故有其重要价值,后文将作分析。南宋人陈耆卿《赤城志》卷四十又指出孟观有一首类似的诗:
旧传“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为杨文公幼时诗。《邵氏闻见录》又云:舒州峰顶寺有李太白题云:“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前二句既不同,而其说复异。今天台华顶峰有孟观诗云:“偶因华顶宿,抬手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盖华顶一峰天台山之最高者,故观诗有此语。今峰傍有摘星岭,因诗立名,则前所指为太白、文公语,疑好事者改之尔。(陈耆卿《赤城志》卷四十,四库全书本)
这段话一方面点出杨亿作“危楼”诗的传言,一方面引了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的话,说“舒州峰顶寺有李太白题诗”云云——邵氏将此诗的地理位置弄错,可见此事流传过程中的以讹传讹。一方面陈氏又指出南宋人孟观在天台华顶峰有一首题诗,与李白诗字句略同,并由此怀疑李白、杨亿的诗都是“好事者”伪造。《全宋诗》第七十一册,据此将此诗收入孟观名下,题名《登华顶峰》,成为他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首诗。
二
仔细分析一下宋人上述有关史料,可以发现,不管他们是有真知灼见者,还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者,其实都没有否认李白曾经在某个山寺做过一首诗,只不过在判断这首诗与流传的一些宋人诗作之间的关系时,一些人与宋人作品混同,导致时地模糊,区分不清,由此产生种种歧说而已。宋人的一些颇似矛盾的记载,不但不足以否定王得臣最早记载的《夜宿乌牙寺》诗为李白所作,反正印证此诗在宋代流传甚广,模拟者众多的事实。这首诗的妙处在后两句,因此在众多记载中,不管前两句如何改换,后两句却丝毫没有变动。只要我们理解宋初人有模拟唐人诗的风气,便可以了然由李白的这首《夜宿乌牙寺》演化出宋人的《题峰顶寺》《危楼》《登华峰顶》等作品的原因所在。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有一则论“古今诗人多以记境熟语或相类”者,举例如韦应物云“野渡无人舟自横”;
寇莱公云“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杜子美云“坐饮贤人酒,门听长者车”;
荆公云“室有贤人酒,门多长者车”。唐人云“万井闾阎皆禁火,
九原松柏自生烟”;
圣俞云“千门皆禁火,九野自生烟”等。并谓:“诸名下之士,岂相剽窃者邪?”(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文莹《湘山野录》卷上谓:“寇莱公诗‘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之句,深入唐人风格。”也不以寇准几乎完全模仿韦应物的诗句为剽窃。实际上,几位宋人改李白诗的首句为“夜宿峰顶寺”或“危楼高百尺”以为己诗,都是这种风气的反映。这一点似乎在宋初诗人中特别明显,王禹偁、杨亿、晏殊等人模拟李白的作品都可作如是观,它们的存在与李白的《夜宿乌牙寺》诗本来毫不矛盾,但由于在流传过程中渐渐与宋人模拟之作混同,导致李白这首诗的著作权反遭质疑,则纯属误会。对于有人据王禹偁或杨亿等人诗句而伪造李白诗碑的说法,笔者认为不能成立。乌牙寺为一人迹罕到之地,将宋人的几句诗改换一下,在此地伪造出一块李白诗碑,目的何在呢?正因为这里人迹稀少,因此李白这首题诗被人抄去流传世间,而一般人并不明了其真相,这样解释似更为合理些。
据此,笔者推断:在曾阜于乌牙山发现李白诗碑之前,此诗实际上已在宋初广为流传,只不过人们不知道其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李白而已。笔者作出这一推断,还有一个重要旁证:苏轼《真兴寺阁》诗中有一句“引手攀飞星”,这句诗很可能化用了李白的“举手扪星辰”(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有意思的是,南宋王十朋《集注分類东坡先生诗》(四部丛刊影印宋务本堂刻本)卷二注此句,谓苏轼用李太白诗“危楼高百尺”云云。王文诰辑注本则改为:用杨文公诗“危楼高百尺”云云。这些都间接证明此诗文本、作者之间之混乱。苏轼此诗作于嘉祐年间,此时距离曾阜元丰初年发现李白诗碑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旁证“举手扪星辰”这些诗句在当时已经流传。如果说王禹偁、杨亿、晏殊三人少年时都曾经吟诵过这首诗的话,只能推断为:正因为这首诗在宋初已流传甚广,但不知为何人所作,故他们改动其中若干字句,吟诵出来,时人便以为是他们的创作了,甚至被附会为他们“幼颖悟”“号为神童”等的证据了。
从上引《邵氏闻见后录》《湘山野录》等的记载看,类似的诗句模拟在宋人看来并不为过,寇准的诗句在有宋一代流传甚广,被视为其平生得意之句即是明显的例子。但问题在于:流传为杨亿等人的作品已经与他们的“幼颖悟”“号为神童”等传说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李白诗碑没有被发现之前,很多人是将这些诗句视为杨亿等人的原创的,这一点与寇准等人的模拟在性质上是有所不同的。
宋人文献中,除了王得臣《麈史》和刘宰《漫堂集》主张李白此诗作于“蕲州乌牙寺”,其诗第一句为“夜宿乌牙寺”之外,支持此说的还有赵子崧的《朝野遗事》,所言与王得臣几乎完全一样,当是抄自王书(赵书已佚,文见《永乐大典》卷八百二十三所引)。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十七“乌牙山”条,也明确此诗为李白所作。并谓“南乌牙山有灵峰院,在黄梅县东北五十里,有白居易所撰碑”云云,更可以作为《夜宿乌牙寺》诗为李白所作的确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该根据宋人王得臣、刘宰、赵子崧、王象之等人的记载,确定《夜宿乌牙寺》诗为李白之作,并恢复其诗的本来面貌。童养年先生《全唐诗续补遗》卷三亦据《舆地纪胜》之说,增补李白此诗,题名为《乌牙寺》,甚有见地
(见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但愿这一成果早日为李白研究界所接受,将其正式收入李白诗集中。根据诗碑中“布衣李白”署名,可以推断:此诗并非少年之作,所谓“天上人”乃指在山顶佛寺中禅定之高僧,此种情境、心境绝非不知世事之儿童所能言,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首诗必是“少年之作”,当代一些学者推断其为“少年之作”,是因为心目中先有那几首宋人模拟之作的缘故,而这一点与李白写作此诗是毫无关系的,绝不可混淆。笔者推断:这首诗应是李白“酒隐安陆”时期,曾短期南下蕲州,参黄梅之禅,而作于乌牙山峰顶禅寺中。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