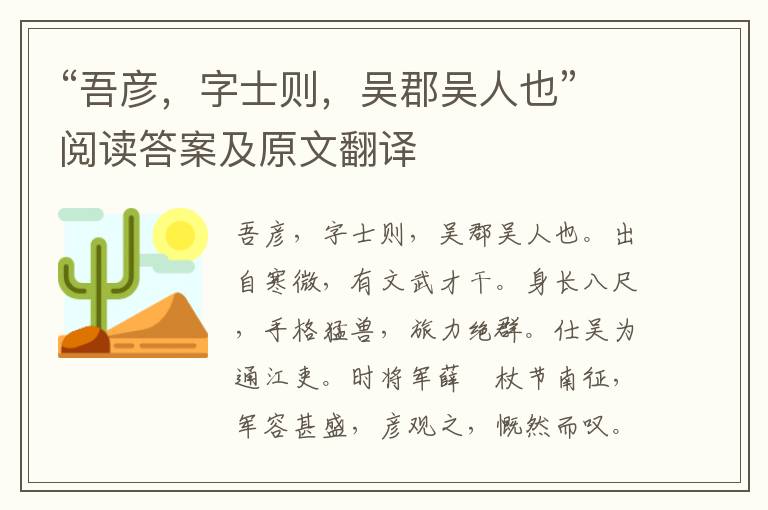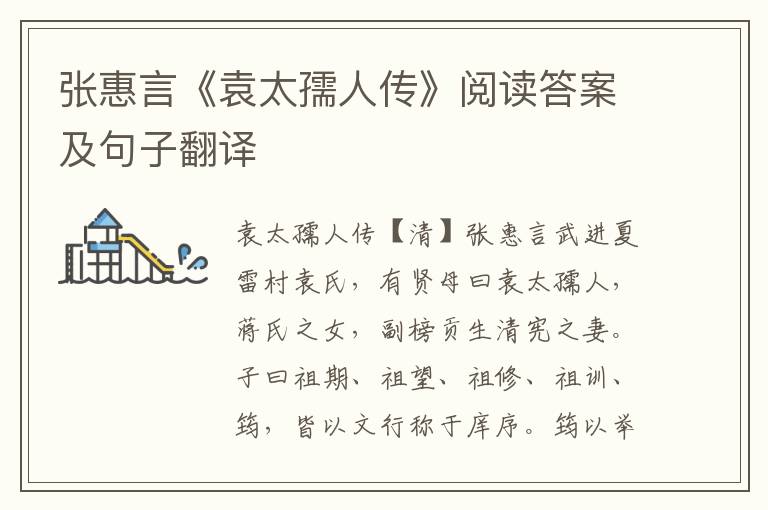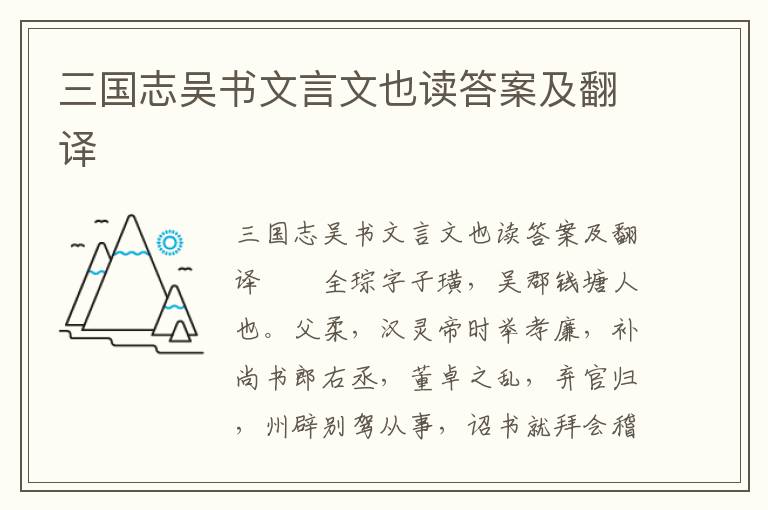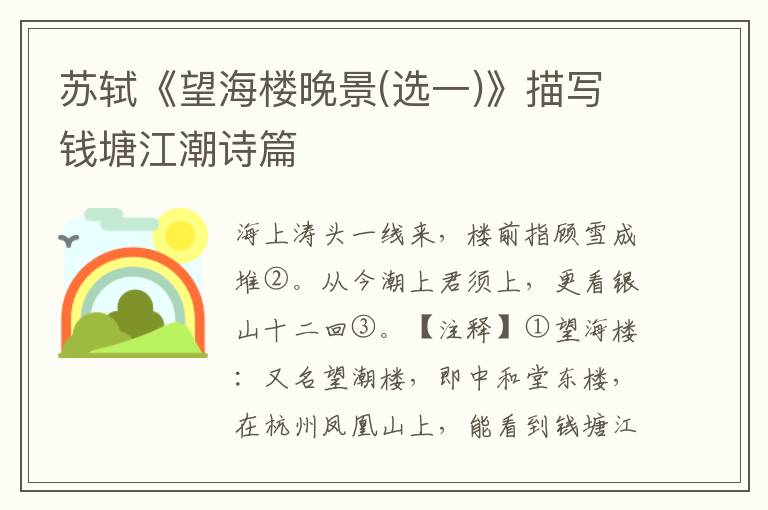【简介】感谢网友“雕龙文库”参与投稿,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方便大家学习。
张志和现存著作很少,据学者考证,仅有《玄真子》三卷,诗词九首,诗词均见载《全唐诗》卷三百零八。①使他获得崇高文学史地位的则是五首《渔歌子》词,尤其是首阕,已成文学史和词史上的名篇。
还是让我们先来细读张志和的五首词作吧。词曰: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钓台渔父褐为裘,两两三三蚱蜢舟。能纵棹,惯乘流,长江白浪不曾忧。
霅溪湾里钓鱼翁,蚱蜢为家西复东。江上雪,浦边风,反著荷衣不叹穷。
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莼羹亦共飡。枫叶落,荻花干,醉泊渔舟不觉寒。
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歌还。钓车子,掘头船,乐在风波不用仙。②
首阕首句中的“山前”,本作“山边”,今依吴本《尊前集》、《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唐诗纪事》、《诗话总龟》、《诗人玉屑》,改作“山前”。
《渔歌子》,唐教坊曲,《金奁集》入黄钟宫。其调式为单片“七七三三七”,二十七字,四平韵。现存最早作品即为唐张志和所撰《渔歌子》五首。这组《渔歌子》在流传和接受的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甚至成为封建文人的心灵慰藉和精神家园。但是,这组词中的地名,特别是“西塞山”、“长江”、“青草湖”、“巴陵”等所指究竟为何处,长期以来一直有分歧,迄今未有定论。笔者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仔细辨析,多方求证,终于弄清楚词中地名的确切所指。
先来看第一首。此阕中的“西塞山”,并非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中所言大冶(今湖北黄石)“西塞山”,而是皮日休《西塞山泊渔家》诗中所言之“西塞山”,即地处今浙江湖州西郊弁南乡樊漾湖村境内的西塞山。南宋山水画家李结曾卜居于此,作《西塞渔社图卷》,并请好友范成大、周必大等人题跋,范跋云李结“经营苕、霅间”,“不胜健羡”,冀“候桃花水生,扁舟西塞,烦主人买鱼沽酒,倚棹讴之,调赋沿溪,词使渔童樵青辈,歌而和之。清飚一席,兴尽而返。松陵具区,水碧浮天,蓬窗雨鸣,醉眠正佳”。其人其事其情,俨然张志和再世。按:唐肃宗尝赐张志和奴婢各一,志和配为夫妻,名夫曰“渔僮”,妻曰“樵青”,事见颜真卿《颜鲁公集》卷九《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一文。而倪思《经鉏堂杂志》卷一“张志和”条则径云:“吴兴人指南门二十余里下菰、菁山之间一带远山为西塞山也,山水明秀,真是绝境。”此外,明栗祁《万历湖州府志》卷四记载:“尚书严震直墓在西塞山。”按:严震直为明初乌程即今湖州人,官至工部尚书,号西塞山翁。因此,当地村民又称西塞山为尚书坟山。陈子龙《吴兴》诗云:“更闻西塞下,渔唱落轻舟。”清官修《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二十二云:“西塞山,在乌程县西南二十五里,有桃花坞,下有凡常湖。唐张志和游钓于此,作《渔父词》曰:(略)。”陆心源、周学浚等纂《湖州府志》卷十九亦云:“西塞山,在城西二十五里。唐张志和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下有桃花坞、凡常湖,张志和游钓于此。”此类记载,尚有不少。
历代文献记载足以证明,浙江湖州也有一西塞山,唐张志和《渔歌子》词所言西塞在湖州。然直至俞陛云先生撰《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仍以为“词言‘西塞’、‘巴陵’、‘松江’、‘霅溪’、‘钓台’,地兼楚越,非一舟能达,则此词亦托想之语,初非躬历”,将张志和笔下的“西塞”、“巴陵”,视为“楚地”。其实,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九即已辨明:“有两西塞,一在霅川,一在武昌。案《唐书·张志和传》,谓颜真卿为湖州刺史,志和来谒,真卿以舟蔽漏请更之。志和曰:‘愿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又志和词中有‘霅溪湾里钓鱼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霅川。而在武昌乃曹武成王用师之城。洪内翰作《西塞渔社图》,亦尝辨此。而《漫录》乃谓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见亦误矣。”可惜未能引起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
按:樊漾湖,位于西塞山北侧,面积今约百亩,西塞山水流入该湖,经七里玄通江北走,汇入西苕溪。不过,当地村民则呼其为“青草湖”。访诸耆老,言樊漾湖本名青草湖,因雨季经常山洪泛滥,水势湍急,霅然有声,故又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泛霅湖”。汉代名将樊哙驻军西塞山时,适逢洪水暴发,便率领军民抗洪抢险,制服水患。当地居民为纪念樊哙,遂谐“泛霅湖”之音,称为“樊常湖”,意谓樊将军永在。又将湖边的便民庵改为樊哙庙,供奉樊哙神像,香火不断。后来,“樊常湖”又被谐音为“凡常湖”、“樊漾湖”、“凡洋湖”。自张志和《渔歌子》词出,樊漾湖与西塞山便紧密相连,成为湖州重要的文化景观和旅游资源,成为历代高人胜士的留连之地。
在了解西塞山、樊漾湖地理位置的基础上,再来看第一首词的一、二两句,词人垂钓的地点已大致可定。白鹭生息之地,必有大片水域以供觅食,有茂密树林以供栖息,可知词人当背山面湖垂钓,山乃西塞山,湖则樊漾湖。湖水之流动极为缓慢,钓者既观“桃花流水”,则所在多半临江;钓者又见“鳜鱼肥”,则所在多半临湖,盖江、湖交汇处,水中氧气充足,营养丰富,为游鱼溯洄产卵、生息之所,当然也是渔人、钓者盘桓之地。“桃花流水”、“鳜鱼肥”这两个条件兼而有之,则所处多半是江、湖即玄通江与樊漾湖的接合部,亦即第三阕所言“霅溪湾”。
接着看第二首。此阕中的“钓台”,并非富春江上的严子陵钓台,而是湖州城西二十里许西苕溪上被称作“石堂子”的大礁石。此石与西塞山相望,仅三里之遥。据了解,石上原有钓台遗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州航运管理部门为了疏通西苕溪航道,多次轰炸此石,没能成功,只得在石上安装航标灯塔。与“钓台”相应,“长江白浪不曾忧”之“长江”便是指西苕溪。洪水泛滥时节,西苕溪急流直下,白浪翻滚,威势与凶险不减长江。按:中原惯呼水为“河”,江南则惯称水为“江”。这里的“长江”,固然是用泛称为特称,指代西苕溪;但也不排除是作者自矜胸襟阔大,借长江以自豪,用的是双关的修辞手法。
钓台既距西塞山不远,桃树又是南方极寻常之果木,而鳜鱼亦太湖流域习见之物种,故西苕溪钓台也能像第三首中的霅溪湾一样,可以同时满足“西塞山前白鹭飞”与“桃花流水鳜鱼肥”两个条件。如此说来,第一首词竟有些像概述,是这五首词的总领、统辖,所言垂钓地点可以兼指西苕溪钓台和霅溪湾。不过,笔者以为,在西苕溪钓台垂钓的隐喻、象征意味,要远大于它的实际意思。因为当流而钓,其安全、便捷、舒坦和成效都不及岸边,但那份孤迥绝尘、临清瞰远、擅奇含秀的心灵体验,却是居岸垂钓难以拥有的。或许,这就是词人先钓台而后霅湾的缘故吧。两相权衡,将首阕所言钓捕地点定在霅溪湾,似更合乎情理。
那么,第三首中的“霅溪湾”,又在何处呢?先说“霅溪”。霅溪,亦称霅川,指苕溪自湖州至太湖段。按:苕溪有二,出天目山之南者为东苕溪,流经临安、余杭、德清诸县;出天目山之北者为西苕溪,流经孝丰、安吉、长兴等县。两溪在湖州城西杭长桥合流后,亦因水流湍急,霅然有声,遂称霅溪。霅溪北流三十里,歧分为众多港汊,分别经由环城河、小梅、新塘、长兜、大钱诸道口注入太湖。
前文已言,西塞山下的青草湖或曰樊漾湖,有一条约七里长的水流与西苕溪相连,名曰玄通江,玄通江与青草湖的交接处,就是霅溪湾。如首阕所描绘,霅溪湾确是垂钓的好去处,后人干脆叫做钓鱼湾。宋末元初湖州人韦居安《梅诗话》卷下有云:“乡人钱牧叔谦别墅在西门外,地名张钓鱼湾,即唐人元真子张志和钓游处。水亭三间,扁曰‘鱼湾风月’,诸公多有赋咏。”可见,垂钓霅溪湾的优游、闲逸甚至风雅,是西苕溪钓台所不及的。再往后,连“张”字也省去。《万历湖州府志》卷四云:“钓鱼湾,(乌程)县治北三里,张志和钓鱼处。”董斯张《崇祯吴兴备志》卷十五云:“钓鱼湾,在乌程县西三里,古称张志和钓鱼处。”
紧接着的“江上雪”,所言又为何处何物?答:这里的“江”即苕溪,“雪”指芦花,当地俗呼为“苕”。唐人杨倞注《荀子·劝学》即云:“苕,苇之秀也。”宋人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三十六“苕溪”条引《耆老传》云:“夹岸多苕花,每秋风飘散,水上如飞雪然,因名。”
还有“浦边风”之“浦”。《说文解字》:“浦,濒也。”《玉篇》:“水源枝注江海边曰浦。”晋周处《风土记》:“大水有小口别通曰浦。”故此“浦”不是泛指,而是定向指“霅溪湾”。另外,还可以从词意获得佐证。此阕首句言垂钓,乃静处溪湾;次句言舟行,是漂泊水上。第三句紧承第二句,言舟行所见情景;第四句则照应首句,言垂钓时的感受。唯其风中敛志静思,末句之出才显得十分自然。按:“荷衣”一语,因屈原《离骚》之“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从而具有高蹈避世的隐逸内涵。《文选六臣注》吕延济注孔稚珪《北山移文》云:“芰制、荷衣,隐者之服。”
事实上,这一首是张志和自道其生计和行踪。据颜真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一文记载:“真卿以舴艋既敝,请命更之。(志和)答曰:‘傥惠渔舟,愿以为浮家泛宅,沿泝江湖之上,往来苕、霅之间,野夫之幸矣!’”
再来看第四首。首句“松江蟹舍”之“松江”实指松陵镇,“蟹舍”则指以蟹飨客的人家。按:松江,在苏州吴江境内,上接太湖,为吴淞江源头,盛产大闸蟹;在松江与太湖交接处,松陵镇宅焉,为吴江县治所在。宋人范成大《吴郡志》卷十八:“松江,在郡南四十五里,《禹贡》‘三江’之一也。……今按:松江南与太湖接,吴江县在江濆。垂虹跨其上,天下绝景也。”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松江”条云:“唐人诗文称松江者,即今吴江县地,非今松江府也。松江首受太湖,经吴江、昆山、嘉定、青浦,至上海县合黄浦入海,亦名吴松江。”松陵在太湖东南,湖州在太湖正南,以小舟出湖州小梅口,一个时辰即可到达,往来非常便捷。
最后看第五首。此词中的地名,其歧解有过于首阕者。事实上,首句中的“青草湖”,与岳阳洞庭湖无关;上文已经说明,青草湖是西塞山旁樊漾湖的本称、俗称。方志中则多称凡常湖。宋人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三:“凡常湖,在(乌程)县西二十七里。”清徐凤衔《乌程县志》卷三云:“凡常湖在县西二十七里,受西塞山之水而入龙溪。西塞山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按:东、西二苕溪,当地统称为龙溪。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二句中的“巴陵渔父”,在这里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比喻,是作者借《楚辞·渔父》中的渔父以自况,手法与第三首末句之“荷衣”相类,起到前后呼应和卒章示意的作用。按:巴陵(今湖南岳阳)与洞庭是屈原被流放时的历经之地,屈原曾临湖写下《湘君》、《湘夫人》等著名诗篇;屈原一直都处于进退、用藏的矛盾之中,曾因此受到巴陵渔父的嘲笑和劝导。张志和于此乃借言渔父,表示要选择一种与屈原不同的、避世远害的生活态度和人生道路。
故五首词中,唯“巴陵”不是实指。这是创作的需要。从题旨看,“巴陵渔父”不但是本首的“词眼”,也是五首词共同的“词眼”,是作者借《楚辞·渔父》彰显自己对高洁、自由人格精神的追慕和矜守。俞陛云先生所谓“托想之语”,仅此一“巴陵渔父”耳。
有学者认为,志和曾贬“南浦尉”,应该到过楚地,“巴陵”为确指。其实,颜真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一文已经说得很清楚:“寻复贬南浦尉,经量移,不愿之任,得还本贯。”可见志和并没有去南浦(今重庆万州)就任。此其一。其二,词中既言“钓车子”,可见目的在于垂钓,又言所乘乃“掘头船”,是一种头尾不显著的简陋小船。以一叶小舟而能横泛太湖、长江、洞庭,恐怕不太现实;纵能,也艰险无比,恐怕很难会有边划船边唱曲的轻松悠闲。而且,说词人从太湖一路钓捕到洞庭,然后才回来,也不通情理。故“巴陵”绝非确指,而是借用。
顺便说一说“钓车子”。钓车子,又叫钓车,就是轮竿,亦即在鱼竿上装一个线轮以放线收线。唐人韩愈、元结、张籍、李商隐、陆龟蒙、徐寅等人的诗中,均曾写到钓车,陆龟蒙诗中更是多次吟咏。宋代著名画家马远所作《寒江独钓图》中,鱼竿上也装有轮子。
仔细玩味,末章第二句内涵丰富,颇有深意。既自称“巴陵渔父”,又言“还”,而客观上不可能乘一舟往来于洞庭、太湖,故此“巴陵渔父”必为“托想之语”无疑,而由一“还”字则曲折可知词人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选定挣脱名缰利锁,回到夙愿中的世外桃源,去过清苦艰难却自由自在的洁净生活。一路“棹歌”,充分体现出词人在找回真淳自我后的轻快和愉悦。末尾三句,更是进一步具体表现这种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无待于外的、自给自足的欣慰和满足。
据颜真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大历九年(774)秋八月,在颜真卿湖州刺史任所,有一场六十余人参加的盛大雅集。席间,张志和挥毫泼墨,进行与《渔歌子》同类题材的绘画创作,“或挥洒横抪而纤纩霏拂,乱枪而攒毫雷驰。须臾之间,千变万化,蓬壶仿佛而隐见,天水微茫而昭合”,引得“观者如堵,轰然愕贻”。又,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云:“(志和)自为《渔歌子》,便画之。”沈汾《续仙传》卷上亦记载:“真卿为湖州刺史日,与门客会饮,乃唱和为《渔父词》。”《全唐诗》卷八百二十一皎然《奉应颜尚书真卿观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歌》一诗,亦佐证志和所绘确系太湖景观。此外,志和之兄松龄(即鹤龄),恐其弟浪迹江湖不返,遂于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城东买地结茅斋以居之。志和于大历九年(774)作《渔歌子》词五阕,松龄随即“和答弟志和”一阕以劝其归。词云:
乐在风波钓是闲,草堂松径已胜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
词中明言“太湖水,洞庭山”,又是一证。按:太湖中有洞庭山,分东、西二山。东山古称胥母山,又名莫厘山,原系湖中小岛,元明以后始与陆地相连成半岛;西山为太湖中最大岛屿,古称包山,一作苞山,又名夫椒山。东、西洞庭山,皆为太湖名胜之地。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张志和五首《渔歌子》词所描述的,都是以湖州为活动中心的太湖地区的风土景物,作者借分咏西塞山、钓台、霅溪湾、松江和青草湖的渔钓生活,从不同角度表达隐逸的志操与乐趣。这组词与其绘画相互配合,彼此映照,形成一个文化整体。本书所要讨论的则是单纯的词体创作。
从孕育环境、激发因缘和创作时间来看,这组写于逝世前不久的《渔歌子》,无疑是张志和一生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
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在其名著《艺术哲学》一书中,将种族、环境、时代列为影响人类文明的三大因素;其中,环境,首先是指自然环境。①事实上,人作为生物进化的产物,始终在接受自然环境的包围、陶冶和熔铸;即使在今天,人类的生命和生活仍必须主要依赖自然,审美的资源和标准仍主要是自然。就中华民族而言,自然审美始于魏晋六朝,催生出山水诗;到唐代则开始取得辉煌成就,孕育出山水田园诗派。张志和的《渔歌子》便是从这样的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一株奇葩。
从自然环境看,《渔歌子》所描写的是太湖沿岸的生活情景。太湖流域濒临江湖河海,气温水柔,草木茂盛,山川秀丽,水网密布,物产丰富,渔猎樵采种植皆宜。水有柔滑的一面,又有凶险的一面,虽“望之多烟云之思”,而“涉之或风波之惧”②。层叠的山峦,纵横的河道,茂密的草木,缤纷的色彩,这样复杂多变的环境,固然倍增探索、驾驭的艰险,但也使人们变得机警灵活,适应性强。所以,在江南水乡泽国、丘陵山地生长的人们,既具柔慧之资,又有悍勇之质,柔中寓刚,刚柔并济。六朝以来,江南文化更多表现柔的一面,但刚的一面继续存留,唐宋时代的江南文化仍体现出柔中寓刚的特征。李绅《过吴门二十四韵》诗有云:“里吟传绮唱,乡语认歈讴。……旧风犹越鼓,余俗尚吴钩。”元稹《春分投简阳明洞天作》诗亦云:“郡邑移仙界,山川展画图。……似木吴儿劲,如花越女姝。牛侬惊力直,蚕妾笑睢盱。……闾阎随地胜,风俗与华殊。”白居易《和微之春日投简阳明洞天五十韵》和曰:“勾践遗风霸,西施旧俗姝。”①直到晚唐,诗人仍感叹:“噫嘻尔风师,吴中多豪士。”②随着南北交融的深入,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江南逐渐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地区,江南士大夫往往多才多艺,且集风流与儒雅、柔慧与刚勇、豪迈与隐忍、精致与务实、开放与包容等多种南北文人的不同特征于一身。骆宾王、贺知章、张旭、顾况、贯休,当然还有张志和,皆杰出其间。在《渔歌子》词中,实际上也隐含了两种价值取向和精神品质,即乐观豪放、拼搏进取与委运任化、闲适旷迈,显露出南北融会、儒道合一的特征。也许正是这种品质和特征,使《渔歌子》成为后来同类作品企慕的典范。
从创作时间看,张志和写这组《渔歌子》时,已度过十多年隐居生活,处世态度、思想性格都非常成熟和稳定。当然,这是就作者的立场和毅力而言;在超旷闲适的外表之下,其实也包扎着悲凉和冲突。一个像“巴陵渔父”那样“西复东”四处漂泊的人,却口口声声说自己“不须归”、“不曾忧”、“不叹穷”、“不觉寒”、“不用仙”,潜台词是否正好相反?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选择和现实处境甘之如饴,早已习与性成,浑然不觉,是不会产生这么清醒而强烈的自我警戒意识的。当然,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张志和的评价;相反,我们对他能以坚定的隐逸姿态对抗尘世,放射出高洁的人格光辉,奉献诚挚的敬意。如果把五首《渔歌子》进行一番比较,不难发现,后四首都在念念不忘自己迥异世俗的生存姿态,只有第一首最多自然描写,最少自我意识。五首之中,只有这一首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自有道理。
我们还可以从这组《渔歌子》的激发因素,来烛照张志和的心灵地图,探索他的心路历程,加深对作品本身的理解。颜真卿守湖州,志和即往见之,以《渔歌子》与真卿等人唱和;又在当年的湖州集会上现场泼墨,技惊全场;而去世又那么奇特,且极可能是有意为之的水解。这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是否有一条贯穿其间的线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条线索就是张志和似乎急于向世人宣布什么,演示什么,证明什么。那么,宣布什么呢?从他答谢颜真卿赠舟时所言“愿以为浮家泛宅”诸语,可推断他是在强调隐逸心志;当众挥毫,且技惊全场,则演示高人乃在世外;以词调相唱和,则进一步演示“野夫”以“民调”吟唱隐逸生活的旨趣;戏水自沉,则是以看似独特、实则效仿屈原的死亡方式向世人证明方外高人宁赴清流而死的迥异凡俗的决绝与英勇。这么分析,或许有求之过深的嫌疑,但公元774年张志和一连串惊世骇俗的举措,又令人不能不这么思考。
如此看来,《渔歌子》从诞生之日起就已拥有丰邃的文化学意义,而非一般的词体创作了。一言以蔽之,即隐逸文化。它既是张志和本人隐逸思想、理想的表白,也是一般企慕、尝试隐逸的人们所追求的高境,更是广大失意赍恨者可以用来抵抗俗世、逍遥游方的精神乐园。丹纳说:“无论什么时代,理想的作品必然是现实生活的缩影。”①同样,张志和的《渔歌子》也是时代投影于其心灵的产物。
张志和十六岁即蒙德宗赏识,擢明经,赐美名,任职内廷,诚可谓少年得志,恩荣备至。但也许正因为过于顺利,少不更事,对可能到来的人生打击缺乏最基本的心理预警和承受能力。果然,受宠爱不久,便坐事远贬,既而丁忧,雪上加霜,终于一蹶不振,乃至看破红尘,从此浪迹江湖,一去不返,借老庄哲学作遁世的甲胄。当然,这些都是按常理推论所得。因为追求功名事业是人类自我实现的本能,是天赋人权,没有不得已的伤心事,绝望至极,有谁愿意退隐水滨林下,与草木虫鱼鸟兽为伍?事实也证明,年轻的张志和是积极入世的,而进退用藏的转折点又出现在遭受打击之后。这就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是年轻的张志和承受不了现实的撞击而遁世作“逍遥游”的。
但自我实现、祈求永生是世间一切事物的本能要求,即使最脆弱的生命,也会竭力进行光合作用,开花结果。“博学,工辞章,事亲孝”,“严奉家庙,恤诸孤”,“立朝正色,刚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天下不以姓名称,而独曰鲁公”②的颜真卿,就是张志和的雨露和阳光啊。颜真卿守湖州,对于本人来说,是人生的一个低谷;但对于张志和而言,也许就是企盼已久的、唯一的自我实现的机会。张志和何等聪明,当然要及时把握,紧抓不放,借以怒放自己生命的光华。笔者以为,这也许就是张志和为何一年之内急于完成那么多人生重大事件的缘由和驱动力。
如此分析,则《渔歌子》已然成为一组光风霁月的弥撒曲和安魂曲。看似超迈洒脱、闲逸俊发的逍遥游,原来竟是英勇悲壮、视死如归的天堂之旅!
张志和的《渔歌子》在中唐时期出现,并且一出现就大受欢迎,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它昭示了中唐时期的时代精神和审美风尚已发生重大转变,“不是对人世的征服进取,而是从人世的逃遁退避”,“心灵的安适享受占据首位”①。沿着这个内转继续向心灵的纵深处蔓延,便到达晚唐五代最为敏感、细腻的神经末梢。这个时代气运与浙江地域文化相结合,便孕育出了晚唐五代浙江词。
①参阅陈耀东《张志和著作考》,载《浙江学刊》1982年第1期。
②曾昭岷、曹济平等编著《全唐五代词》(上),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5-26页。
①[法]丹纳著《艺术哲学》第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唐)韦夏卿撰《东山记》,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苑英华》卷八百二十九。
①《全唐诗》卷四百四十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62页。
②吴融《祝风三十二韵》,见《全唐诗》卷六百八十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871页。
①[法]丹纳著《艺术哲学》第四编第二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页。
②(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三,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854、4859、4861页。
①李泽厚著《美的历程》第八章《韵久之致》,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